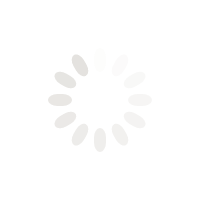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扫罗波尔马特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米manbet手机版我的四位祖父母都是在20世纪初从东欧犹太城镇和村庄移民到美国的。manbet手机版这是一代贫穷但乐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期望新理性主义的世界将利用教育和创造力抛弃边界、边界和宗教,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manbet手机版(比如,我母亲的父亲,虽然他在二战期间在造船厂焊接,后来经营一个三明治摊,但他的业余爱好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依地语文学和历史教师。)manbet手机版因此,他们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父母,都成为了教授,我的母亲,费利斯·戴维森·珀尔马特,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我的父亲,丹尼尔·d·珀尔马特,从事化学工程,这也许并不奇怪。
manbet手机版米manbet手机版我的四位祖父母都是在20世纪初从东欧犹太城镇和村庄移民到美国的。manbet手机版这是一代贫穷但乐观的知识分子,他们期望新理性主义的世界将利用教育和创造力抛弃边界、边界和宗教,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manbet手机版(比如,我母亲的父亲,虽然他在二战期间在造船厂焊接,后来经营一个三明治摊,但他的业余爱好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依地语文学和历史教师。)manbet手机版因此,他们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父母,都成为了教授,我的母亲,费利斯·戴维森·珀尔马特,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我的父亲,丹尼尔·d·珀尔马特,从事化学工程,这也许并不奇怪。
manbet手机版我母亲的工作生活充满了研究合作,她组织了这些合作,在专业和个人方面都很享受。manbet手机版社会工作领域里到处都是热情友好的人,他们乐于彼此合作。manbet手机版我父亲的工作包括用计算尺和图表(这两者对小时候的我都很有吸引力)进行仔细而准确的计算,用实验室设备做实验,还有他耐心地教授和指导的研究生。manbet手机版周末,我们家满是父母的朋友,讨论政治、电影、书籍和艺术,一直讨论到深夜。manbet手机版对世界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关切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manbet手机版在这种氛围下,我从小就想要了解所有的“语言”——音乐、文学、数学、科学、符号、建筑、心理学——尤其是那些似乎最普遍的语言。manbet手机版我认为manbet手机版每个人都manbet手机版我们需要知道宇宙丢失的“所有者手册”里有什么,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并“使用”它。manbet手机版我和两个妹妹希拉、托娃就读的贵格会学校鼓励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关怀;manbet手机版在基础的数学和科学课程上有优秀的老师,但(当时)在这些领域没有太多的基础知识来鼓励进一步的创造力。manbet手机版相反,我很兴奋地学会了清晰而有表现力的写作,并熟悉了非科学的方法。
manbet手机版和许多科学家一样,音乐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manbet手机版我不知道音乐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是否有文献记载,但似乎有共同的元素,也许从练习乐器时固有的延迟满足开始。manbet手机版以我为例,我的小提琴老师Frances Duthie(她是我在学校里唯一一位经常教我的老师)确实教了我一种强烈的完美主义道德,但这是基于一种温暖、人文的人际交流传统,以及协作、共享倾听和贡献的室内乐理想。manbet手机版在我的一生中,通过弦乐四重奏演奏和集体演唱,团体音乐创作的乐趣一直延续着——我最喜欢的科学团体经历也有一些同样的感觉。manbet手机版(多年后,作为伯克利大学的教授,我很高兴有机会为本科生设计“物理与音乐”课程。)
manbet手机版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想我会追随我对大哲学问题的迷恋。manbet手机版在我看来,有两大谜团:世界是如何运作的?manbet手机版以及大脑是如何工作的?manbet手机版(后者也与前者有关,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大脑感知世界。)manbet手机版因此,1977年开始在哈佛学习时,我考虑过哲学和物理双学位——直到我意识到如果我这样做,就没有时间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了。manbet手机版我决定先主修物理,因为似乎我以后更有可能回到哲学,而不是反过来。manbet手机版(我们将会看到)。
manbet手机版于是,上大学成了学习许多领域课程的机会。manbet手机版我对当时相对较新的认知科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manbet手机版我发现生物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枯燥乏味,需要死记硬背。事实上,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新概念被发现。manbet手机版我了解到物理是一项非常社会化的活动,每周都有一群朋友和室友聚在一起解决数学和物理问题。manbet手机版我还发现,几乎没有时间去消化你在本科学习的物理学的含义——当我1981年毕业时,我很好奇继续读研究生,最终有机会专注于物理学。
manbet手机版我选择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因为我想要从各种各样强大的实验研究小组中选择,而这似乎是伯克利所提供的远远超过其他顶尖物理系的东西。manbet手机版当我开始读研究生时,我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有真实数据(而不仅仅是理论)的研究项目,来解决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manbet手机版最可能的路线是粒子物理加速器实验,我希望最终能这样做;manbet手机版但首先,我想我应该看看我是否能在一个更小的小组项目中学习。manbet手机版在我的第二年,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由理查德·穆勒教授领导的不寻常的、充满活力的、折衷的研究小组。
manbet手机版里奇遵循——也许是超越了——他导师的传统manbet手机版Luis Alvarezmanbet手机版追求有趣的研究课题,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以一种“我能行”的实验主义者的态度——以及对所有主张的严格怀疑。manbet手机版当我加入小组时,小组成员正在每周会议上报告他们的工作:(1)一个新的基础物理实验的想法,测量木星对星光的引力偏转;manbet手机版(2)机器人望远镜超新星搜索测量哈勃常数;manbet手机版(3)对大气碳进行拉曼散射测量,研究碳循环;manbet手机版(4)台式回旋加速器,用于放射性同位素测年;manbet手机版(5)寻找各向异性的宇宙微波背景测量;manbet手机版(6)各种各样的话题,包括路易斯最近和他儿子为解释恐龙灭绝而提出的撞击理论的含义。manbet手机版这是物理学家最擅长的传统:玩转思想,制造玩具。manbet手机版(注意:物理学家在玩!)
manbet手机版我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机器人望远镜超新星项目上,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种基本测量方法——哈勃常数的可能性。manbet手机版我最终开发了一种软件(和一点硬件),可以自动识别图像中的超新星,并排除小行星和宇宙射线等混淆来源。manbet手机版我一直都很喜欢玩电脑,最新的电脑速度已经足够快,内存也足够大,可以进行近乎实时的图像分析,从而引发超新星的后续研究。manbet手机版1986年,当我博士毕业时,自动超新星搜索已经成功启动并运行,我被要求留下来做博士后,从这个项目中得到结果。manbet手机版(在此过程中,我当然被里奇小组的无数主题所吸引,我的论文实际上使用了相同的机器人望远镜和图像分析技术来寻找我们太阳的一颗可能的伴星,这是他们提出来解释的manbet手机版周期manbet手机版地球上每隔2600万年就会发生大灭绝——恐龙的灭绝只是其中之一。)
manbet手机版1980年,当里奇开始哈勃常数项目时,所谓的II型超新星看起来很可能被用作测量距离的指示器,其校准基于巴德-韦塞林克膨胀光球法(后来由我的共同获奖者研究)manbet手机版布莱恩•施密特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但到1986年该项目启动并运行时,有证据(由古斯塔夫·塔曼和他的学生布鲁诺·莱本古特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表明,Ia型超新星的新子分类可以用作另一种(也许更好的)距离指标。manbet手机版这个消息促使卡尔·彭尼派克博士(Rich团队中更资深的研究员)和我思考对新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manbet手机版Ia型超新星明显比II型超新星亮得多,所以原则上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研究。manbet手机版自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批超新星被研究以来,人们一直希望有一天它们能被用来测量宇宙膨胀的减速——现在,新的Ia型亚分类的一致性为重新审视这一想法提供了可能性。manbet手机版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工具来开发Ia型超新星:在机器人超新星搜索中,我们使用了第一代“电荷偶装置”探测器,用于超灵敏的天文成像,我们还开发了图像分析工具,可以筛选CCD产生的大量数字数据。
manbet手机版1987年年底,卡尔和我提出了一个新项目:我们要设计和建造一个新的宽视场相机,在4米级望远镜上配备CCD的最宽相机,并开发软件,在一个晚上搜索数万个星系。manbet手机版不像我们之前的机器人超新星搜索,在每张图像中研究一个星系,这种方法将允许我们一次观察数千个更遥远的星系。manbet手机版我们估计,在几年内,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发现足够数量红移高达~0.3的超新星,从而可以很好地测量减速参数。manbet手机版该项目于1988年在我们持怀疑态度的导师里奇的支持下启动,是伯克利新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的创始项目之一。
manbet手机版在澳大利亚赛丁斯普林斯的英澳4米望远镜上,该项目开始缓慢,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计划有十几个晚上,只有两个半晚上天气好。manbet手机版尽管如此,到1992年,当我被要求接替里奇成为超新星研究小组的领导者时,我们发现了一颗z = 0.45的Ia型超新星——是世界上高红移样本的两倍。manbet手机版这是当时已知的最高红移超新星。manbet手机版(另一种高红移Ia SNe是由Norgaard-Nielson领导的丹麦团队在几年的搜索中发现的。)manbet手机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利用这一成功获得了其他大型望远镜(有更可靠的天气)。
manbet手机版两个关键问题阻碍了我们的研究:关联高红移和低红移超新星的亮度(用不同的滤波器测量);manbet手机版并保证提前发现遥远的超新星,并及时测量它们的峰值亮度。manbet手机版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人们就无法获得研究它们所需的大型望远镜的时间。manbet手机版到1994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能够保证整“批”的多颗高红移超新星,它们都在变亮,而且都是在预先选定的日期发现的,非常适合安排亮度和光谱的测量。manbet手机版这样的“保证”让我们提出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新用途:对遥远超新星的精确测量,这对我和我的合作者Ariel Goobar(当时是伯克利的博士后,现在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已经证明可以用来区分宇宙学理论的超远z~1超新星尤为重要。
manbet手机版与此同时,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开发了几种方法来进一步校准Ia型标准蜡烛:大卫·布兰奇(David Branch)表明,根据颜色进行选择可以给出一个标准化的集合,而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则表明,可以在亮度峰值和亮度变亮和变暗曲线的时间尺度之间建立关系。manbet手机版在Calan/Tololo超新星搜索(由Mario Hamuy, Jose Maza, Mark Phillips和Nick Suntzeff领导)中发现了一个漂亮的低红移超新星数据集,这使得这些改进的校准得以进行。manbet手机版因此,到1994年底,在我们确定了批量发现和多波段跟踪高红移超新星的有效方法之后,我们现在的国际科学家团队全天候工作,为此目的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望远镜收集新一批高红移超新星的数据。manbet手机版由共同获奖者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组织的一个由经验丰富的超新星研究人员组成的新团队也是如此。
manbet手机版最后,在1997年,我们分析了42颗Ia型超新星的红移manbet手机版zmanbet手机版~0.5,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宇宙的膨胀显然是由一个宇宙常数主导的,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空间的“暗能量”,所以它实际上是manbet手机版加快manbet手机版——这与已知的物理模型不符!manbet手机版我们在1998年1月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上宣布了宇宙常数的惊人证据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因为我们的团队和布莱恩的团队,包括共同获奖者manbet手机版亚当·里斯manbet手机版-在年初的会议上独立宣布了匹配的结果,到年底,大多数科学界已经接受了这一非凡的发现。
manbet手机版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找到什么答案都会令人兴奋:如果宇宙的减速速度足够快,我们就会知道宇宙是有限的,并将在大收缩中结束;manbet手机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可能是无限的,而暴胀理论将是一个成功的预测。manbet手机版我们不可能期待实际的结果,这是一个给基础物理学带来新难题的惊喜。manbet手机版这是一个项目的结论,反过来又启动了许多新的项目。manbet手机版我们现在有一个乐趣,那就是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导致宇宙加速。manbet手机版自1999年以来,我一直在与同事们一起研究这样的新项目,包括开发一种新的空间望远镜,它可以更精确地测量宇宙的膨胀历史。
manbet手机版也许当我和妻子劳拉·尼尔森送我们现在8岁的女儿诺亚上大学时,科学将会给出下一个答案——或者,更好的是,关于我们的世界会有新的令人惊讶的问题。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基金会2019年
manbet手机版本传记于2019年6月提交。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和获奖者
manbet手机版2022年诺贝尔奖
manbet手机版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从古基因组学和化学到记录战争罪行。
manbet手机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