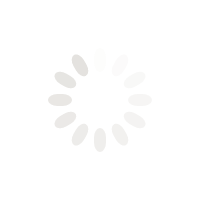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安德烈·海姆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我认为任何人在死前都不应该写自传。manbet手机版”
manbet手机版萨缪尔
 manbet手机版年代manbet手机版几年前,我和一大群英国人在约旦沙漠徒步旅行。manbet手机版我们在露营,像往常一样,晚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我们就围着营火坐着,玩流行的英国游戏“叫我虚张声势”来打发时间。manbet手机版在这个游戏中,一个玩家说了几个陈述,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余的人必须猜测哪个是正确的。manbet手机版所有其他的陈述都被称为“虚张声势”。manbet手机版我取笑我的徒步旅行者和语句像“我出生在地中海气候”,“我是红军的中尉”,“我已经赢得了一个搞笑诺贝尔奖”,“我爬几个五千米高山”,“我摔倒了一个100米深裂缝没有一根绳子的,”我被称为“俄罗斯”首次在32岁的,“我的大学我学习洲际弹道导弹”,“我是北极圈以北的一个砖匠”,“我知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等等。manbet手机版令我惊讶的是,除了最后一条声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虚张声势”,而人们很容易相信,任何俄罗斯人都很熟悉他们的政治领导人。manbet手机版我赢了每一场比赛,因为事实完全相反:除了认识戈尔巴乔夫(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真的。manbet手机版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琐碎。
manbet手机版年代manbet手机版几年前,我和一大群英国人在约旦沙漠徒步旅行。manbet手机版我们在露营,像往常一样,晚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我们就围着营火坐着,玩流行的英国游戏“叫我虚张声势”来打发时间。manbet手机版在这个游戏中,一个玩家说了几个陈述,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余的人必须猜测哪个是正确的。manbet手机版所有其他的陈述都被称为“虚张声势”。manbet手机版我取笑我的徒步旅行者和语句像“我出生在地中海气候”,“我是红军的中尉”,“我已经赢得了一个搞笑诺贝尔奖”,“我爬几个五千米高山”,“我摔倒了一个100米深裂缝没有一根绳子的,”我被称为“俄罗斯”首次在32岁的,“我的大学我学习洲际弹道导弹”,“我是北极圈以北的一个砖匠”,“我知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等等。manbet手机版令我惊讶的是,除了最后一条声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虚张声势”,而人们很容易相信,任何俄罗斯人都很熟悉他们的政治领导人。manbet手机版我赢了每一场比赛,因为事实完全相反:除了认识戈尔巴乔夫(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真的。manbet手机版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琐碎。
manbet手机版不过,就铭文而言,我还没有死。manbet手机版我认为现在写自传还为时过早,因为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已经结束了。manbet手机版我只有52岁,打算积极地继续我的研究工作。manbet手机版然而,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当然!),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我必须提供一本自传。manbet手机版因此,我在下面承认了一种文学练习。manbet手机版虽然我没有详述上面的任何非虚张声势的陈述,但读者仍然可能会发现我的人生道路是非典型的。manbet手机版我不知道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做事的方式,或者这只是一个单独的故事,与我的研究生涯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的时间线结束于1987年,那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manbet手机版在那之后,我的科学传记在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随机漫步到石墨烯”。
manbet手机版苏联的分类
manbet手机版1958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是妮娜·拜尔和康斯坦丁·海姆的次子。manbet手机版在我生命的前七年里,我和我的祖母玛丽亚·齐格勒和祖父尼古拉·拜耳一起在那里度过。manbet手机版我对祖父的记忆很少,因为他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但我的祖母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直到我上大学离开家。manbet手机版七岁的时候,到了上学的时候,我不得不极不情愿地离开索契,与父母和哥哥弗拉季斯拉夫(Vladislav)一起住在纳尔奇克市,他们在那里工作。manbet手机版纳尔奇克是卡巴尔迪诺-巴尔卡利亚共和国的首都,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在世界地图上可以找到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所在地,靠近臭名昭著的车臣。manbet手机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学校时光,但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会回到索契和我的祖母呆在一起。
manbet手机版在这一点上,提到我的种族起源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苏联的某些群体来说,种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常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最终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manbet手机版我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manbet手机版尽管苏联人口有很大的民族多样性(1989年的官方人口普查列出了100多个民族),当局设法通过在苏联护照上有一个特殊的线(“第5行:国籍”)来跟踪每一个民族。manbet手机版我护照上这一行写着“德国人”。manbet手机版这是因为我父亲来自所谓的伏尔加德国人,他们是18世纪在伏尔加河沿岸定居的德国殖民者的后代。manbet手机版我母亲的血统也主要是德国人。manbet手机版我一直认为我的外祖母玛丽亚是犹太人,但根据我哥哥最近对家族史的研究,她的父亲也是德国人。manbet手机版因此,据我所知,家里唯一的犹太人是我的曾祖母,双方的其他人都是德国人。
manbet手机版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解释我的种族。manbet手机版首先,当然,我苏联护照上的“德国人”一词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读者将在下面发现这一点。manbet手机版其次,在诺贝尔奖宣布后,我的种族问题意外地再次浮出水面——突然间,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奖是英国人、荷兰人、俄罗斯人、德国人还是犹太人。狗万世界杯manbet手机版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似乎很愚蠢。manbet手机版我曾在几个欧洲国家生活和工作过,我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并且不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类,特别是在科学世界这样一个流动的世界里。
manbet手机版老箱子里的骷髅
manbet手机版我对我们家族历史的了解相当粗略,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原因。manbet手机版原因要追溯到我出生前。manbet手机版在斯大林时代,讨论家族历史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故事不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会故意对孩子隐瞒自己的历史。manbet手机版在我申请大学、找工作等时必须填写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manbet手机版在这些文件中,总有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你是否在国外有亲戚,你的亲戚中是否有人是强迫劳动营(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或战俘。manbet手机版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总是真诚地回答“不”,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manbet手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才知道,我家几乎所有人,包括我父亲和祖父,都在古拉格集中营里待了很多年,家里有些人是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我有个叔叔住在巴伐利亚。manbet手机版在我生命的前30年里,这一点被故意而成功地隐瞒了下来。
manbet手机版以下是我从为数不多的在世亲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manbet手机版我的祖父尼古拉·拜耳(Nikolai Bayer)是哈尔科夫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航空制图。manbet手机版1946年,苏联军队在战后的波兰发现的文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佩特里乌拉短暂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的一名初级部长。manbet手机版这段反布尔什维克的过去,加上他的德国血统,以及当时他正在编制东西伯利亚地图的事实,显然足以指控他向日本人泄露国家机密,并将他送到沃尔库塔附近的北部古拉格集中营。manbet手机版1953年斯大林死后,他才被释放。
manbet手机版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他的身后也有一段相当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这是我在多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从他身上学到的。manbet手机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都避免讨论这个问题,即使我问他,他也总是不小心说出来。manbet手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教授物理和数学。manbet手机版然而,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作为一个德意志民族成为了一种政治罪行,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在那里他花了很多年建造一座水电站和一条铁路。manbet手机版1949年,他获准与被驱逐到新西伯利亚的家人团聚。
manbet手机版我还清楚地记得早年的一件事,那就是在索契我祖父母花园的小棚子里,我发现了一个藏在旧箱子底部的一盒旧奖牌。manbet手机版其中之一是圣乔治十字勋章(Cross of St George),这是俄罗斯帝国(革命前)颁发的一种高度军事荣誉勋章。manbet手机版我把我的发现拿给奶奶看。manbet手机版面对质问,她解释说,十字架属于她的父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军医,而其他的装饰则与她的祖父有关,他是德国贵族的后代。manbet手机版19世纪,她的家人住在波兰(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参加了1863年的起义,结果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一个世纪后,那里成为了我的祖先如此熟悉的地方。manbet手机版我再去找那些奖章时,早就不见了。manbet手机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发生后,我奶奶玛丽亚立刻把它们都扔掉了。manbet手机版虽然今天听起来难以理解,但这种行为已经烙印在经历过斯大林主义恐怖的人们的DNA中。manbet手机版她担心我会把奖牌的事告诉我的朋友,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整个家庭都会有麻烦。manbet手机版这发生在赫鲁晓夫时代,当时恐怖已经消退,但“资产阶级”的提醒仍然被“无产阶级”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
manbet手机版到我上学的时候,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苏联体制中消失了。manbet手机版除了一些残余,比如“国籍”界限和所有那些家庭问卷,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最近的恐怖事件。manbet手机版我唯一一次因为我的种族而真正受苦的时候是在试图进入一所顶尖大学的时候,如下所述。manbet手机版除此之外,它只是偶尔在操场上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血腥的犹太人”(“ЖИД”或“Zhid”),因为外国名字通常与犹太人有关(在俄语中,ЖИД这个词听起来非常无礼)。manbet手机版也许是因为后者,我特别热衷于强调我的血液中有一小部分可能是犹太人的。
manbet手机版照常上学
manbet手机版尽管有这样暗淡的家族史,但我自己很幸运,出生晚了,有一个快乐的童年。manbet手机版我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与我的出生地索契有关。manbet手机版我的祖母玛丽亚是一名气象学家,我出生的头几年是在她工作的气象站附近的海滩上度过的。manbet手机版我母亲是一家非常大的真空电子厂的质量控制主管,父亲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相当于西方的首席执行官)。manbet手机版二十年后,纳尔奇克的许多人仍然记得他是一个勤劳和有影响力的人。manbet手机版毅力和勤奋可能是我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品质。manbet手机版我父母的职业使我们家成为苏联技术官僚的顶层。manbet手机版他们不属于享受苏联体制所有特权的共产党精英,而且作为德国人,他们不可能是共产党精英。manbet手机版不过,她们的地位使这个家庭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
manbet手机版我在纳尔奇克的学校被称为专业英语学校,被认为是镇上最好的。manbet手机版尽管它的名字叫英语,但英语教学并不是它的强项。manbet手机版回顾过去,比较一下我们当时是如何被教英语的,以及30年后我是如何被教荷兰语的,在我以前的学校里,英语专业化的概念似乎只是可笑的。manbet手机版另一方面,数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高年级阶段,这主要归功于我们的数学老师瓦伦妮达·塞德涅娃。manbet手机版我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几年后,当我已经是一所精英大学的学生时,当我看到我的旧试卷时,我惊讶于那些试卷的难度和挑战性。manbet手机版其中一些不仅需要回忆能力,还需要想象力和非常规思维。manbet手机版物理和化学也教得很好。manbet手机版我曾经在一个地区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胜,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我对这门学科的热爱,不如说是因为我在几天内就记住了一整本大约1000页长的化学词典(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高兴地被遗忘了)。
manbet手机版我还深情地记得我们的俄语和文学老师奥尔加·佩什科娃。manbet手机版尽管我在这两门课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我并没有在这两门课上取得优异的成绩。manbet手机版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她的课程对学习如何以一种清晰而简洁的方式写研究论文是有帮助的。manbet手机版关于我的学业,除了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苏联洗脑宣传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了。manbet手机版作为一种平衡,学生们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类似的广播电台,这种小小的反叛帮助我们对宣传告诉我们的许多事情(尽管不是全部)产生了健康的怀疑。manbet手机版当然,像我周围的每个人一样,我扮演着一个纪律严明的苏联学生应有的角色。
manbet手机版第一关失败
manbet手机版16岁时,我从学校毕业时获得了一枚金牌,这是一种授予那些在所有科目中都取得满分的人的荣誉(通常是前5%)。manbet手机版我的父母鼓励我去最好的大学,我的目标是莫斯科的几所精英大学。manbet手机版在学校里,我所有的精确科学都学得很好,包括物理和化学,但我最强的科目是数学。manbet手机版然而,我的父母说服我,纯数学没有好的职业前景。manbet手机版因此,我决定学习物理。manbet手机版俄罗斯最顶尖的物理大学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莫斯科物理与技术学院。manbet手机版然而,物理学的入学考试是出了名的竞争激烈和极其艰难,因为我在一个省级城镇长大,我相信它们超出了我的能力。manbet手机版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所顶尖大学——莫斯科工程与物理学院(MIFI)。manbet手机版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从MIFI和Phystech的试卷样本中解决了问题,尽管还不是很自信,但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manbet手机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主要障碍竟然是我的种族。
manbet手机版MIFI的第一次考试是数学笔试,我非常自信,我正确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并将获得“优秀”(俄罗斯学校和大学的评分系统包括四个等级:“优秀”、“良好”、“满意”和“不及格”)。manbet手机版然而,我发现我的成绩只是“令人满意”,更糟糕的是,我的口语数学是“不及格”。manbet手机版我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我准备不充分,以及我在实际考试中缺乏经验:口语考试中的问题似乎比我在家做的MIFI试卷样本要难得多。manbet手机版所以我决定回家,继续学习,一年后再碰碰运气。
manbet手机版间隔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manbet手机版我的父母很支持我,并在他们工作的工厂为我找了一份工作,作为一名负责校准测量设备的技术人员,他们还为我提供了数学、物理和俄罗斯文学的辅导(这些是我所选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manbet手机版几周后,我发现我比我的导师(他被认为是镇上最好的)更懂数学,所以这些辅导课停止了。manbet手机版另一方面,我的物理教程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manbet手机版我的导师是纳尔奇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瓦列里·彼得罗西安。manbet手机版我非常喜欢每一堂课。manbet手机版我们解决了许多来自物理或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旧试卷上的问题。manbet手机版但更有帮助的是他教我处理物理问题的方法:如果你先猜测可能的答案,解决问题就容易得多。manbet手机版物理水平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了解多个物理领域,通常涉及几个逻辑步骤。manbet手机版例如,在五步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可能性很快就会出现分歧,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得到最终答案。 If, however, you try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from both ends, guessing two or three plausible answers, the space of possibilities and logical steps is much reduced. This is the way I learned to think then and I am still using it in my research every day, trying to build all the logical steps between what I have and what I think may be the end result of a particular project.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my tutor no longer asked me to write up a solution. Instead, I just explained verbally the way I would solve a particular problem – all the logical steps required to get to its end without describing routine details. This allowed us to go through the problems at lightning speed.
manbet手机版我还从俄罗斯文学的辅导课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manbet手机版我的导师说我写得很好,但从我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我试图回忆和重复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思想,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担心自己的思想不够有趣、重要或正确。manbet手机版她的建议是试着解释我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偶尔使用那些权威的短语,以支持和加强我的写作。manbet手机版这个简单的建议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manbet手机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比我的同学更善于用文字解释我的想法。
manbet手机版国家公敌
manbet手机版经过这一年的紧张准备,我觉得我知道的足够多了,比前一年更有信心,为MIFI做好了准备。manbet手机版我轻松地解决了数学笔试中的所有问题(还是第一名),完善了陈述,并期望获得“优秀”的分数。manbet手机版然而,在接下来的考试(口语数学)中,我被告知这个分数只是“不错”,而且主考官拒绝解释哪里错了,也不给我看剧本,即使剧本就在他面前。manbet手机版他又给我出了三个难题,是我所见过的最难的。manbet手机版我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问题,部分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但有一个小错误,并为第三个问题提供了正确答案。manbet手机版然而,我无法解释我是如何想到这个答案的。manbet手机版这个答案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还记得:答案是998。manbet手机版我通过这些努力得到的分数是“令人满意的”,这显然不足以让我被大学录取。manbet手机版除了考官相当严厉的对待之外,我还注意到这次考试更奇怪的地方——除了我之外,同一间教室里(大约20名考生)没有一个人取得“令人满意”的分数;manbet手机版他们都失败了。 Even more curiously, the names of all the candidates were either Jewish- or foreign-sounding. I went to look at the lists of people in other examination rooms and most of the names sounded Russian, with a very few exceptions.
manbet手机版即使是像我这样naïve的人,在17岁的时候,很明显,有一项政策是不让某些少数民族失望的。manbet手机版事后看来,这很容易解释,因为这所特殊的大学专门研究核物理,在当时,如果你是犹太人或德国人,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移民,会了解“国家机密”,然后出国。manbet手机版这在苏联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威胁。manbet手机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一项政策,甚至是一项可以理解的政策,只是没有大肆宣传。manbet手机版几年后,我发现有一些犹太人就读于MIFI,并成功毕业。manbet手机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父母必须去找克格勃在MIFI的代表(他们在苏联的每一个组织中都有所谓的“第一部门”),说服他们,他们的孩子是可靠的苏联公民,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manbet手机版显然,这些策略确实起了作用,但我甚至可能我的父母都没有想到这是必要的。manbet手机版或者,也许我的父母太清楚我家庭问卷中的真实谎言了。
manbet手机版偶然的物理学家
manbet手机版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官方层面的歧视,非常震惊。manbet手机版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另一所大学试试运气。manbet手机版我对自己说“管他呢”,然后申请了物理科技。manbet手机版我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经历,因为它与MIFI是如此不同。manbet手机版考官很友好,甚至乐于助人,考试问题很有趣,整个环境都很友好。manbet手机版我觉得好像有人不小心把我放在了一个错误的房间里,远离了行刑队的检查官。manbet手机版也许,情况就是这样。
manbet手机版我的考试成绩远远超过了入学的门槛,尽管四次考试中我只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分数,其余的都是“不错”。manbet手机版我觉得我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的MIFI经历仍然很新鲜,那些失败的考试记忆不断浮现,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有时还影响了我对问题难度的判断。manbet手机版这一点在我的物理口语考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至今记忆犹新。manbet手机版给我的第一道题看起来很简单,我很快就解决了,但考官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manbet手机版我试图提出抗议,过了几分钟我们才明白,我已经解决了一个比他给我的要难得多的问题;manbet手机版即使我解决的问题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仍然是错误的。manbet手机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manbet手机版所以,当给我第三题时,考官反复问我是否确定我理解了所问的问题。
manbet手机版在物理科技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招生面试,我很害怕我的种族问题会再次出现,尽管我的成绩很好,他们可能不会录取我。manbet手机版众所周知,在面试的基础上,有时分数略低于门槛的考生被录取,分数高于门槛的考生被拒绝。manbet手机版种族问题确实以“你的德语水平如何?”manbet手机版我回答说“差不多”,然后开始思考还能补充什么。一位小组成员(Seva Gantmakher,甘特马克尔效应)很快插话说:“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了。”manbet手机版事实证明,这句话,以及他随后的干预,使我走上了固态物理学的道路,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
manbet手机版像许多那个年龄的准学生一样,我梦想着从事天体物理学或粒子物理学,渴望解决“宇宙中最大的谜团”。manbet手机版但是在Phystech的应聘者中有一个谣言,说这样说会被面试官认为非常naïve。manbet手机版我记得这一点,但不想作弊。manbet手机版所以,当被问及我的抱负时,我说我想研究中子星(真的),因为我想了解物质在极高密度下的表现(一个借口,听起来不是这样naïve)。manbet手机版塞瓦立即回复说:“很好,你可以在我们的(固体物理)研究所学习高压物理。”
manbet手机版那次面试的另一个记忆是被要求估计地球大气的重量(通常会给应聘者一些棘手的心理问题来解决)。manbet手机版我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在脑子里计算这些数字(大气压力乘以地球表面积除以重力,都是国际标准单位),当我给出一个以万万亿千克为单位的答案时,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我只需要给出一个大概的答案,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manbet手机版我就是这样进入物理科技的。manbet手机版最后,我被MIFI拒绝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Phystech是一所两级以上的大学。manbet手机版我没有先去那里的唯一原因是,我不相信我能胜任。manbet手机版基本上,环境迫使我做出第一个选择,而不是第二个!
manbet手机版所有格林林的母亲
manbet手机版Phystech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大学,不仅以俄罗斯的标准来看,它被认为是crème de la crème,而且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大学相比也是如此。manbet手机版它没有出现在任何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唯一原因是它是一所纯粹的教学型大学。manbet手机版(在俄罗斯,教学和研究传统上是分开的——研究主要在科学院进行,教学则在大学进行)。manbet手机版除了非常严格的学生选拔之外,物理学院如此优秀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与其他苏联大学不同,所有的专业课程和一些通识课程都是由来自莫斯科地区各地学院研究所的实践科学家教授的。manbet手机版当然,在西方,让活跃的研究人员开设本科课程是一种标准,但在俄罗斯却是例外。
manbet手机版更重要的是,作为物理技术专业的学生,我们被迫思考并在我们学习的每一件事中找到逻辑,而不仅仅是记忆事实和公式。manbet手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Phystech的考试风格:当涉及到专业科目时,我们每年参加的许多考试都是开卷的。manbet手机版这意味着,只要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公式,就不需要记住公式。manbet手机版相反,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需要结合不同的学科领域,从而教会我们真正理解科学,而不仅仅是记忆。
manbet手机版从成立的那一刻起,Phystech就由苏联著名科学家领导,如manbet手机版Kapitsa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兰道manbet手机版还有很多其他的。manbet手机版在我自己的讲师和考官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伊曼纽尔·拉什巴、弗拉基米尔·波克罗夫斯基、维克多·利德斯基、斯巴达克·别利亚耶夫、列夫·皮塔耶夫斯基、伊萨克·卡拉特尼科夫和列夫·戈尔科夫,仅举几例。manbet手机版我不得不承认,当时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告诉我太多东西,这得益于我不太擅长听课的事实。manbet手机版直到最近,我才重新发现了其中一些名字,当时我在自己的旧考试证书上看到了他们的签名。诺贝尔奖宣布后,Phystech公司把这些证书放在了网上。狗万世界杯
manbet手机版Phystech的工作量很大,课程极具挑战性。manbet手机版可以说,我们关于量子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和经典力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来自Landau-Lifshitz理论物理课程。manbet手机版也许它们不是本科生最好的教科书,但它们是预期成就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示。manbet手机版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应付这种教学方式带来的心理压力,一些学生退学不仅是因为成绩不好,更多的是因为精神崩溃。manbet手机版我个人认识几个有自杀倾向和精神问题的学生。manbet手机版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每次考试后都要喝一些酒来释放累积的压力,这也许拯救了我的理智。
manbet手机版前两年半的基础课程特别难。manbet手机版在那之后,随着我们进入专业课程,压力减轻了。manbet手机版从第三年开始,我们开始在所谓的科学院基础研究所参加讲座。manbet手机版就我而言,我选择了切诺戈洛夫卡的固体物理研究所,因为我喜欢高密度的中子星。manbet手机版从第五年开始,我们也开始在研究实验室工作——不是一些专门设计的本科项目,而是真正正在进行的项目,在那里我们作为学术研究团队的一部分工作。manbet手机版第六年是硕士的一年,100%以研究为基础。manbet手机版在那之后,正常的途径(如果你想留在学术界)是两年的研究试用期,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有资格获得博士学位,再持续3年。manbet手机版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个长达11年的过程——在物理科技工作6年,再加上5年的“viva”,即论文的口头答辩。
manbet手机版对我个人来说,在Phystech的前半年是一场斗争。manbet手机版我来自一个省城,而我的一些同学毕业于莫斯科的精英学校,专攻物理和数学。manbet手机版不少人是国际奥林匹克物理或数学竞赛的冠军。manbet手机版最初几个月的主要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达到这些人的水平;manbet手机版在正规科目上,他们比我们快了将近一年,尤其是数学。manbet手机版直到我在第一次年中考试中拿到了所有的最高分之后,我才开始对这个神童般的环境有了足够的信心,并开始有所放松。manbet手机版尽管有压力和拷问,但我们每一个从Phystech毕业的人都有那些艰难岁月的美好回忆,并为我们的母校感到最自豪。
manbet手机版跟着潮流走
manbet手机版我从物理学院毕业时拿到了所谓的“红色文凭”,这意味着我在班上排名前5%到10%。manbet手机版期末考试50分左右,我只有两个“好”。manbet手机版其中一门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我毫不羞愧地将其归因于我在这门课程中找不到任何逻辑。manbet手机版相比之下,我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获得了“优秀”,直到今天,我对阅读仍有美好的回忆manbet手机版《资本论》manbet手机版我偶尔会引用他的话来取笑,或者让我的西方同事感到震惊。manbet手机版我的第二件“好事”是列夫·戈尔科夫(Lev Gorkov)教授的超导课程,他也是我的主考人。manbet手机版对Phystech来说奇怪的是,他不允许我们在考试期间使用教科书(他真可耻),而我在其中一个推导中犯了一个错误。manbet手机版这很有趣,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当我已经是荷兰的一名教授时,超导成为了我的研究课题。
manbet手机版尽管我考试很成功,但我不认为我在班上的学生中特别突出。manbet手机版在我上学的那一年里,有一两个学生只有“优秀”的成绩,有些学生学习得比我更深,对课程的理解也比我更好。manbet手机版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地尽力;manbet手机版我努力学习,以保证自己获得最高分,并保持在班上的第一名。manbet手机版我在这方面很成功,但并没有花费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manbet手机版事实上,在我的大学时代,我根本不是一个模范学生。manbet手机版由于成绩优异,我通常有资格每半年获得一次奖学金,但它经常(四五次)被取消,作为对我的惩罚,因为我错过了一些强制性的讲座,假期休息迟到,组织考试后的聚会,有时会让一些人进医院,以及类似的不当行为。manbet手机版缺课通常是允许的(除非是政治课程),我设法错过了大部分讲座。manbet手机版我从课本上学习,参加小组辅导,除非我不喜欢某些导师。manbet手机版我不会把这种学习方式作为成功的秘诀推荐给有抱负的学生,但它可能很适合一些人,就像它适合我和我班上的其他一些学生一样。
manbet手机版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我做得还可以,但没有尽我最大的努力,这种态度贯穿了整个大学和博士时期。manbet手机版直到很久以后,当我成为一名独立研究者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喜欢上物理,并为了物理本身而竭尽全力。
manbet手机版从崇高到荒谬
manbet手机版我的硕士项目的主题是金属的电子性质,我通过在超纯铟的球形样品中激发电磁波(所谓的螺旋波)来研究。manbet手机版从螺旋共振中,我可以提取这些样品的电阻率信息。manbet手机版这项研究的竞争优势是我所使用的铟的极端纯度,因此在低温下,电子可以在与样品直径(~1厘米)相当的距离上发射。manbet手机版毕业后,我开始在同一个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这是许多物理学毕业生的习惯。manbet手机版回顾过去,就我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而言,读博的那五年似乎非常平淡无奇。
manbet手机版我读博士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成为我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扰动:从一个研究所搬到另一个研究所。manbet手机版那时,我的博士导师维克多·佩特拉肖夫(Victor Petrashov)从固体物理研究所搬到了新成立的微电子技术研究所。manbet手机版尽管两者相距只有200米,但这意味着工作严重中断,损失了一些设备,并重新安装了一切。manbet手机版最初,我满怀热情地做金属物理研究,但随着我意识到可能除了我的导师之外,没有人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兴趣,这种热情逐渐消退。manbet手机版然而,在教育方面,那些年对培万搏manbext官网养实验技能和让我的手指变得“绿色”非常重要。manbet手机版这段经历在我未来的研究生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石墨烯的故事。manbet手机版在这方面,我非常感谢维克多,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技巧的实验家之一。manbet手机版在鞋带和密封蜡的帮助下,他可以做出惊人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切诺戈洛夫卡的研究实验室里,通常只有鞋带和密封蜡。
manbet手机版我遇到不少人怀念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但我自己即使在切诺戈洛夫卡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时代,那是一个相当精英的学术场所。manbet手机版在我的记忆中,几乎任何对研究重要的材料的到来,无论是铜线还是GE清漆,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原因,几乎等同于一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到达西方。manbet手机版有一次,维克多很幸运地借到了一个美国制造的闭锁放大器来做一些测量,而我们通常必须使用苏联的等效放大器(“等效”一词并不能描述两者之间的全部差异)。manbet手机版在短短几周内,我就能得到我用“同等”方法无法想象的结果。manbet手机版资源的可用性(或缺乏资源)基本上决定了我可能做什么。manbet手机版我相信,那些自称见证了“苏联科学的伟大”的实验家,要么属于那些在顶尖院士中有赞助人的少数人,要么更有可能是自欺欺人,选择相信过去的天空比现在更蓝。
manbet手机版话虽如此,在苏联,实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manbet手机版理论学派非常强大,尤其是人们所说的"朗道理论学派"manbet手机版那些人做事的水准是最高的。manbet手机版这种力量的根源部分在于教育,但也在于苏联理论家的工作方式。manbet手机版我通过参加许多研究研讨会见证了这一点。manbet手机版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和激烈的辩论上,没有不能问的问题,也没有不能质疑的权威。manbet手机版在西方,这种风格仍然被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经验”的苏联科学家所铭记。manbet手机版对参与者来说,这可能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有时我真的很怀念这种风格。manbet手机版这种怀旧情绪通常出现在今天的科学文献中偶然看到某些论文之后:如果它们首先在这样的研讨会上发表,甚至作者都不敢把它们付梓。manbet手机版这些辩论非常有影响力,使人们能够更快地学习,并对物理学的许多领域形成广泛而明智的观点。 I myself benefited greatly from such seminars and consider them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y education in Chernogolovka. Many of the seminars I attended were organised by Seva Gantmakher. His care for detail and breadth of experimental knowledge were a great example for me and my fellow students.
manbet手机版尽管理论系的氛围很好,但即使是理论家也受到苏联科学状况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最优秀的理论家都搬到了西方。manbet手机版我不认为更好的生活条件是人才流失的唯一原因:理论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manbet手机版他们通常是在与实验主义者的互动中诞生的,因为实验结果是新想法的触发器。manbet手机版在切诺戈洛夫卡完全缺乏这一点,因为用现有的设备很难取得新的成果,如果有可能的话。manbet手机版在我读博士的时候,苏联的实验科学已经衰落到这样的地步,人们认为,对一个实验主义者来说,达到名声和荣耀的顶峰最合适的途径是证实一位杰出的苏联理论家提出的理论。manbet手机版实际上,切尔诺贝利戈洛夫卡的许多实验学家就是这样做的。
manbet手机版这就是我的科学生活。manbet手机版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生活,忙得不可开交。manbet手机版切诺戈洛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漂亮的郊区,周围都是森林,安静而宁静。manbet手机版生活总体上是愉快的,尽管我的生活条件艰苦到极点——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住在宿舍里,和另外两个年轻的研究员合住一个房间。manbet手机版我的一个室友是谢尔盖·杜博诺斯(Sergey Dubonos),多年来他成为了我的固定合著者,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石墨烯论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nbet手机版除了研究,我的其他爱好是登山和泛舟。manbet手机版每年,从高加索到中亚,我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苏联各个角落的山上和河边旅行,有时一年内要旅行四次。manbet手机版这些旅行经历经常与Max Maximenko和Phystech的朋友Stas Ionov分享。manbet手机版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Irina Grigorieva,她也在邻近的固体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manbet手机版她后来成为我的合作者,对石墨烯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manbet手机版在某种程度上,切诺戈洛夫卡为科学家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几乎没有任何干扰,这使我们能够专注于研究。manbet手机版除了排几个小时的队买香肠和奶酪(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度过。manbet手机版即使没有太多热情,我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发表了几篇论文,取得了应有的进展。manbet手机版但直到我成为一名独立研究者,特别是在1990年搬到西方之后,我才开始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我在诺贝尔奖演讲“随机漫步到石墨烯”中所描述的那样。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传记是在获奖时撰写的,后来以丛书形式出版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这些信息有时会以获奖者提交的附录进行更新。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和获奖者
manbet手机版2022年诺贝尔奖
manbet手机版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从古基因组学和化学到记录战争罪行。
manbet手机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