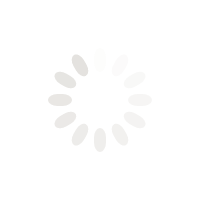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Albert Fert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1938年3月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卡尔卡松。manbet手机版后来,直到我两岁,我一直住在法国南部的另一个城市图卢兹,我的父母是高中教师,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是经济学家。manbet手机版但是战争即将来临。manbet手机版我父亲在1939年6月入伍,也就是我弟弟出生前两个月André。manbet手机版1940年,他被德国人俘虏,成为战俘;manbet手机版直到1945年,他才回国。manbet手机版在战争期间,我和哥哥被送到祖父母在蒙特克拉尔的农场生活,那是Pyrénées山麓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庄。manbet手机版我的母亲继续在图卢兹教书,她每个周末都来看我们。因此,直到七岁,我都过着乡下孩子的生活,挤山羊奶,在祖父的葡萄园里收获葡萄,为兔子或野兔设陷阱。manbet手机版我生活在离动植物世界很近的地方,离物理世界很远。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1938年3月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卡尔卡松。manbet手机版后来,直到我两岁,我一直住在法国南部的另一个城市图卢兹,我的父母是高中教师,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是经济学家。manbet手机版但是战争即将来临。manbet手机版我父亲在1939年6月入伍,也就是我弟弟出生前两个月André。manbet手机版1940年,他被德国人俘虏,成为战俘;manbet手机版直到1945年,他才回国。manbet手机版在战争期间,我和哥哥被送到祖父母在蒙特克拉尔的农场生活,那是Pyrénées山麓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庄。manbet手机版我的母亲继续在图卢兹教书,她每个周末都来看我们。因此,直到七岁,我都过着乡下孩子的生活,挤山羊奶,在祖父的葡萄园里收获葡萄,为兔子或野兔设陷阱。manbet手机版我生活在离动植物世界很近的地方,离物理世界很远。
manbet手机版1945年6月,父亲从战俘营回来,我们一家人在图卢兹团聚。manbet手机版我成了一个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男孩。manbet手机版我父亲一边继续在高中教书,一边准备他的博士论文。manbet手机版最终,他被提升为图卢兹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他对电子显微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manbet手机版我哥哥和我努力学习小学和中学的功课。manbet手机版我们的父亲关注着我们在科学上的进步。manbet手机版毫无疑问,他对严谨思考的偏好对我学习数学和物理的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manbet手机版我的理科成绩很好。manbet手机版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也对文学、艺术和体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manbet手机版十四岁时,我开始打橄榄球,并为被选为我们高中队的队员而感到自豪。 At the age of seventeen, having completed my studies for the baccalauréat, I found myself drawn to Paris and above all to 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 not only because it was a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but also because it had the added attraction of being in the center of Paris, close to the Latin Quarter and St. Germain des Près, and at the heart of the city’s intellectual life. I worked hard to prepare for the competitiv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t the ENS,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 was accepted. In September 1957, I lightheartedly left Toulouse for Paris and 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manbet手机版19岁到24岁之间,我在法国师范学院Supérieure度过了一段非常紧张的青春时光。manbet手机版在乌尔姆街这个小校园里,我的生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接触不同学科的学生,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历史等。manbet手机版此外,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巴黎,有博物馆、展览、电影院、音乐厅和爵士俱乐部。manbet手机版我成了爵士乐、摄影和电影的狂热爱好者。manbet手机版我写了一个剧本,拍了一部电影。
manbet手机版如果我没有跟着优秀的物理老师学习,我可能就会偏离对科学事业的追求。manbet手机版特别是雅克·弗里德尔,他在硕士阶段建立了一个物理项目,让我接触到了凝聚态物理的最新发展,并强调了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的深入教学。manbet手机版正是这个项目吸引我开始研究凝聚态物理学。manbet手机版1965年,当我从军队服役回来时,我在雅克·弗里德尔指导的奥赛固体物理实验室里,在伊恩·坎贝尔的指导下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manbet手机版我有幸得到了论文题目:“测试的建议manbet手机版内维尔莫特manbet手机版(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铁磁性金属中电子的迁移率取决于它们自旋的方向相对于它们的磁方向”。manbet手机版在我的论文研究过程中,我迷上了物理。manbet手机版我发现,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研究人员的工作可以打开许多扇门——前提是他的实验执行得很好,并得到了严格的解释。manbet手机版我在论文中的发现,以及我对电子传递物理学的深入了解,使我有可能在15年后回到这个主题,并发现了巨磁电阻。manbet手机版当我看到我在早期的发现构成了今天自旋电子学的很大一部分基础时,我仍然感到惊讶。
manbet手机版然而,当我在1970年为我的论文辩护时,现有的技术不允许在巨磁电阻和自旋电子学方向上进一步发展。manbet手机版虽然在我的论文中关于三元合金的实验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GMR的概念,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将其扩展到多层的情况,因为当时不可能产生足够薄的层。manbet手机版因此,自旋对铁磁性金属中电子迁移率的影响的开发不得不推迟到1980年代中期。manbet手机版在利兹大学获得博士后职位后,我回到奥赛,在南巴黎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在固体物理实验室指导一小批博士生和博士后。manbet手机版1976年,我被提升为教授。manbet手机版Marie-Josée我住在巴黎;manbet手机版阿丽亚娜(Ariane)和布鲁诺(Bruno)分别生于1968年和1971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把时间分配给了家庭生活和非常持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manbet手机版暑假期间,我们回到了地中海和Pyrénées,回到了我父母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滨海班纽尔斯的家。manbet手机版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研究活动涉及了许多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manbet手机版我的第一个博士生Alain Friederich的论文揭示了霍尔效应和磁阻的各向异性与自旋轨道耦合有关的问题。 Today the Spin Hall effec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physics. I think that some of our results from that period should have an impact on spintronics today. In 1975, in order to interpret our results on the Hall effect and the anisotrop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lectrons and magnetic impurities, I began a collaboration with Peter M. Levy, a theorist at New York University.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years, I spent many summer month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learned to love the city, Greenwich Village and its jazz clubs, SoHo and its art galleries. My collaboration with Peter Levy on theoretical problems encompassed numerous subjects and, among other results,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existence of Dzyaloshinsky-Moriya interactions in spin glasses. One consequence of these interactions is the triad anisotropy in spin glasses, which was confirmed experimentally in the thesis of my Ph.D. student Dimitri Arvanitis.
manbet手机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微电子领域发展的技术似乎有可能使从纳米厚度的层中生长磁性多层成为可能。manbet手机版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以前的学生Alain Friederich正在Thomson-CSF公司的研究小组开发分子束外延(MBE)。manbet手机版1985年在圣地亚哥参加一个会议时,我和阿兰·弗里德里希在游泳池旁边的一个酒吧里,在棕榈树和星星下讨论我们的工作,我们决定在磁性多层膜的生长和研究方面进行合作。manbet手机版在Thomson-CSF的MBE专家Patrick Etienne,以及我的博士生Frédéric Nguyen Van Dau, Frédéric Petroff和Agnès Barthélémy,以及两位博士后Mario Baibich和Jean-Marc Broto的帮助下,我们的合作在1988年初发现了巨磁电阻。
manbet手机版在我们发现巨大磁阻的那天,我们正在测量几个Fe/Cr多层,一个接一个。manbet手机版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含有最薄的铬层的多层膜的质量。manbet手机版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开始测量铬层最厚的多层。manbet手机版我们确定确实存在磁阻效应。manbet手机版然后我们转向多层,其中铬层逐渐变薄。manbet手机版奇迹中的奇迹!manbet手机版铬层厚度减小越大,磁电阻越大。manbet手机版最终的测量结果,我们在0.9 nm的铬上进行了测量,结果令人震惊。manbet手机版平行和反平行结构的铁层之间的电阻增加了80%!manbet手机版我们刚刚参与了我们称之为巨磁阻(GMR)现象的诞生。
manbet手机版1988年7月初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磁学会议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我们在Fe/Cr多层膜中巨磁电阻的工作成果。manbet手机版然而,我的博士生Frédéric Nguyen Van Dau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他的报告,因此他的论文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应。manbet手机版Peter Grünberg没有参加会议。manbet手机版仅仅在接下来的一周,在勃艮第的Le Creusot举行的国际磁膜和表面会议(ICMFS)上,Peter Grünberg和我能够展示我们各自结果的细节,并对我们的发现在磁界成员中引起的相当大的兴趣进行衡量。manbet手机版在这次会议上,我也能够解释我早期的结果,即自旋对铁磁金属中电子迁移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GMR”的解释。manbet手机版1988年12月我们的文章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之后,磁学界对这种利用磁性纳米结构中电子自旋的新现象的兴趣呈指数级增长。manbet手机版这段时期给我留下了一些温馨的回忆。manbet手机版当我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篇论文快要结束时,我很想知道我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报告。manbet手机版我问主席Bret Heinrich还剩多少时间。manbet手机版他告诉我,鉴于人们对我所呈现的工作的兴趣程度,我想继续工作多久都行。 Every researcher dreams of such a response from the chair. Thanks Bret!
manbet手机版从1989年开始,多层物理和GMR成为越来越多的实验室研究的热门话题和课题。manbet手机版此外,我自己的研究活动也在许多方面扩展。manbet手机版除了Frédéric Nguyen Van Dau, Agnès Barthélémy和Frédéric Petroff的论文中关于Fe/Cr体系的实验工作,我和Agnès Barthélémy一起发展了半经典的GMR理论,补充了Camley和Barnas的理论。manbet手机版我还与纽约大学的Peter Levy和Shufeng Zhang合作开发了GMR的第一个量子模型。manbet手机版1990年,我们开始与密歇根州立大学(MSU)的Peter Shroeder、Jack Bass和Bill Pratt团队合作,研究通过溅射制备的多层材料。manbet手机版1991年,我的博士生Dante Mosca首次观测到Co/Cu体系的GMR和层间耦合振荡。manbet手机版斯图尔特·帕金在阿尔马登几乎同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manbet手机版Co/Cu系统后来成为典型的GMR系统。manbet手机版Jean-Marie George论文中对逆GMR的首次观测是我的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另一个重要成果。manbet手机版从1991年开始,我开始对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团队在几何上的GMR(电流垂直于层的平面)的结果感兴趣(cppgmr)。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young researcher at Thomson-CSF, Thierry Valet, I developed a theory of the CPP-GM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in accumulation. Today, this theory has become essential for many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pintronics. The 1993 Valet-Fert paper in Physical Review is my second most frequently cited paper, coming just after the paper in which we presented the discovery of GMR. Beginning in 1994, I collaborated with Luc Piraux at 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 on studies of CPP-GMR using multilayered nanowires. These studies made it possible to extend the results of MSU to much greater thicknesses and to confirm the length scale linked to the effects of spin accumulation in the Valet-Fert model.
manbet手机版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来说是一段紧张而富有成效的活动时期,在此期间,我们对GMR物理学的发展和自旋电子学基本概念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manbet手机版Peter Grünberg和我与Thomson-CSF、飞利浦和西门子等公司合作,还参与了几个由欧洲共同体资助的项目,以进一步开发新的应用程序。manbet手机版1994年,我们获得了国际认可,“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将磁学奖授予彼得Grünberg和我,美国物理学会将国际新材料奖授予彼得Grünberg、斯图尔特·帕金和我。manbet手机版这也让我震惊,GMR只是磁性纳米结构中自旋开发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的大门——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旋电子学的领域。manbet手机版汤姆逊- csf实验室物理组主任Alain Friederich向我建议,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将CNRS和汤姆逊- csf联合起来,共同探索GMR开辟的前景。manbet手机版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计划,使我们进入了大量的新领域:磁隧道结、半金属铁磁体、自旋注入现象、半导体中的自旋输运……这个项目被接受了。manbet手机版新的实验室,称为Unité混合体质(UMP) CNRS-Thomson-CSF(后来成为UMP CNRS-Thales),于1995年春在距离巴黎大学几公里的科贝维尔建立。manbet手机版实验室与大学达成协议,我在大学里继续教书。manbet手机版从一开始,实验室就召集了我在奥赛的团队,与我们合作的汤姆森- csf团队,以及CNRS的几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Jean-Marie George, Annie Vaurès, Jean-Luc Maurice(此后不久,一个研究超导的团队加入了实验室)。manbet手机版从那时起,正是在这个Unité Mixte CNRS-Thales,我的研究活动在自旋电子学领域的许多方向上取得了进展。 The team has been progressively enlarged with the arrival of new researchers from CNRS and assistant profess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Sud – Abdelmadjid Anane, Manuel Bibes, Vincent Cros, Cyrile Deranlot, Julie Grollier, Henri Jaffrès, Richard Mattana and Pierre Seneor.
manbet手机版我很难准确地描述我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泰利斯实验室的研究活动,因为这一活动已经向如此多的方向发展,并探索了自旋电子学的非常不同的维度。manbet手机版关于这项活动的成果,我只能让读者参考我的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我的团队中相对年轻的成员也获得了独立,并逐步制定了自己的研究计划。manbet手机版Frederic Petroff, Agnès Barthélémy和Vincent Cros对磁隧道结进行了大量和多样化的研究。manbet手机版Agnès Barthélémy在Manuel Bibes的协助下,现在负责磁性氧化物和多铁性材料在自旋电子学中的应用的所有研究。manbet手机版我们关于自旋转移现象的非常重要的研究,主要是由文森特·克罗斯和朱莉·格罗利尔,在阿卜杜勒马吉德·阿纳内和亨利·贾弗斯的帮助下进行的。manbet手机版涉及半导体的自旋电子学由Jean-Marie George, Henri Jaffres, Abdelmadjid Anane和Richard Mattana共同研究。manbet手机版单电子自旋电子学已经成为Pierre Seneor和Frédéric Petroff的领域,而Frédéric Nguyen Van Dau指导各种应用的开发,Jean-Luc Maurice是结构研究的专家。manbet手机版Pierre Seneor, Frédéric Petroff, Jean-Marie George和Richard Mattana正在启动一项分子自旋电子学的活动。manbet手机版他们目前都在Cyrile Deranlot和Karim Bouzehouane、Stéphane Fusil和超导团队的Eric Jacquet的宝贵帮助下参与纳米技术的开发。 As for me, I am making every effort to participate in most of these current activities. I also have been able to devote myself a little more to theory: the modeling of single-electron spintronics with Jozef Barnas at the University of Poznan; the theory of the injection of spin into semiconductors with Henri Jaffrès; the theory of the phenomenons of spin transfer with Peter Levy, Henri Jaffrès, Jozef Barnas.
manbet手机版2007年标志着CNRS/泰利斯UMP活动的一个高潮。manbet手机版它有丰富的新成果和出版物,对我来说,还有大量的科学奖项:4月在东京获得的日本奖;manbet手机版今年5月在耶路撒冷获得沃尔夫物理学奖,12月在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奖。狗万世界杯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当然,诺贝尔奖改变了我的生活。manbet手机版我收到了无数的请求;manbet手机版新的责任即将出现。manbet手机版此外,我渴望回到我的研究项目,并具体化我最近的想法。manbet手机版一个艰难的挑战!manbet手机版我也希望诺贝尔奖将促进整个团队的思狗万世界杯想和信息的积极交流。
manbet手机版最后,我想感谢所有帮助我成为今天的我的人:首先是我的父母和Marie-Josée;manbet手机版还有雅克·弗里德尔(Jacques Friedel)和伊恩·坎贝尔(Ian Campbell),他们是我作为物理学家轨迹上的第一批向导;manbet手机版阿兰·弗里德里希(Alain Friederich),我与他合作,对发现GMR起了决定性作用;manbet手机版Unité Mixte CNRS/Thales的团队,最后,还有在我40年的物理学家生涯中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所有人。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传记是在获奖时撰写的,后来以丛书形式出版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这些信息有时会以获奖者提交的附录进行更新。
manbet手机版看看2022年诺贝尔奖的公告吧
manbet手机版即将到来的
manbet手机版观看直播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