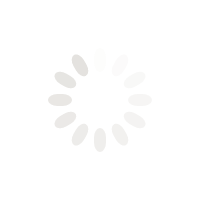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彼得·j·拉特克利夫爵士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我出生于1954年5月14日,在兰开夏郡的卡恩福斯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manbet手机版在当时,我会说这没什么,就像大多数事物如果不进行比较来看一样。manbet手机版我所享受的近乎完全的自由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manbet手机版这个小镇是英国北兰开夏郡一个不起眼的铁路小镇。manbet手机版我父亲是当地的律师;manbet手机版按照习俗,我母亲结婚后辞去了电话接线员的工作。manbet手机版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manbet手机版他们很好,没有过度保护,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从鲁莽的行为中幸存下来。manbet手机版在学业上,我既没有被逼,也没有气馁,我再次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manbet手机版我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是在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我意识到manbet手机版其他manbet手机版人们认为他们是社区里特别的人。manbet手机版我的世界很简单,就是搭树屋、生火、和其他孩子们一起模拟(有时是真的)战斗。manbet手机版但我总是关心改进:更好的弹射器,更热的火焰,更大的爆炸。manbet手机版我对金属的熔化温度了如指掌;manbet手机版熔铅是一种欢乐;manbet手机版创造熔化铁所需的2800OF的雄心壮志令人遗憾地从未实现。manbet手机版我了解到,可以通过压缩数千个小“帽”来制造类似手榴弹的东西,就像玩具枪一样,把它们放在两个大螺栓之间,螺纹在一个螺母上,然后扔向砖墙。manbet手机版结果在附近的车库门上留下了一个整齐的洞。manbet手机版幸运的是,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之前,生命进化了。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我出生于1954年5月14日,在兰开夏郡的卡恩福斯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manbet手机版在当时,我会说这没什么,就像大多数事物如果不进行比较来看一样。manbet手机版我所享受的近乎完全的自由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manbet手机版这个小镇是英国北兰开夏郡一个不起眼的铁路小镇。manbet手机版我父亲是当地的律师;manbet手机版按照习俗,我母亲结婚后辞去了电话接线员的工作。manbet手机版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manbet手机版他们很好,没有过度保护,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从鲁莽的行为中幸存下来。manbet手机版在学业上,我既没有被逼,也没有气馁,我再次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manbet手机版我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是在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因为我意识到manbet手机版其他manbet手机版人们认为他们是社区里特别的人。manbet手机版我的世界很简单,就是搭树屋、生火、和其他孩子们一起模拟(有时是真的)战斗。manbet手机版但我总是关心改进:更好的弹射器,更热的火焰,更大的爆炸。manbet手机版我对金属的熔化温度了如指掌;manbet手机版熔铅是一种欢乐;manbet手机版创造熔化铁所需的2800OF的雄心壮志令人遗憾地从未实现。manbet手机版我了解到,可以通过压缩数千个小“帽”来制造类似手榴弹的东西,就像玩具枪一样,把它们放在两个大螺栓之间,螺纹在一个螺母上,然后扔向砖墙。manbet手机版结果在附近的车库门上留下了一个整齐的洞。manbet手机版幸运的是,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之前,生命进化了。
manbet手机版11岁时,我就读于兰开斯特皇家文法学校。manbet手机版这所学校很好,毫无疑问是我受教育过程中最具形式化的经历。manbet手机版但这并不是田园诗般的。manbet手机版还有一些人回忆起他们在学校供餐方面的经历;manbet手机版20世纪60年代,英国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烹饪国家,兰开斯特皇家文法学校的厨房也不是最受欢迎的manbet手机版蓝绶带manbet手机版国家的。manbet手机版当一顿美餐突然出现时,就不存在均分的问题了:负责餐桌的大男孩们会占绝大多数。manbet手机版同样,在没有比较对象的情况下,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之道。manbet手机版但那幸福的童年已经结束了。
manbet手机版除了英语,我大多数科目都很好。manbet手机版缺乏努力又加剧了我的天赋不足,不幸的是,我的能力越来越差,直到十年或二十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我的精神与学校的精神并不脱节;manbet手机版除了体育运动(尤其是橄榄球)和大学入学(尤其是牛津或剑桥)之外,几乎没有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manbet手机版这种相当狭隘的生活方式确实在适当的时候受到了惩罚。manbet手机版但当时我觉得很舒服。manbet手机版学校有一些好老师;manbet手机版有几部确实很棒。manbet手机版我特别记得加里·斯莱霍姆,他教我化学。manbet手机版重点是在复杂中找到简单,这当然是分子生物学的本质。 I have heard many scientists describe their first appreciation of this, at the hands of some esteemed mentor in a famous research institution. But for me (and I suspect for many others) I’m pretty sure it was the school. Of the two acceptable school options, excellence in sport or Oxbridge entrance, the pathway for myself was the latter, by default. For various reasons I didn’t think I’d enjoy either Oxford or Cambridge, but never had quite the bravery to refuse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which I duly took. Most of the questions were opaque to me, but I remember creating and solving a set of equations relating to a complex chemistry problem. When several variables cancelled out and the answer was simple integer, I felt confident of success. Beyond this I hardly managed a single answer. But rather to my own surprise, and greatly to that of some at the school, a telegram arrived announcing an open scholarship to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Cambridge. This was to study medicine.
manbet手机版我记得当时的决定如下。manbet手机版我原本打算学习化学;manbet手机版我的化学老师鼓舞了我,我父母告诉我,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一位成功的药物化学家。manbet手机版但事实并非如此。manbet手机版有一天,校长约翰·洛林·斯宾塞出现在化学教室里,他是一个相当空灵的人,在这所混乱不堪的学校里走来走去,穿着一件长袍,显得有些不协调。manbet手机版“拉特克利夫,”他说,“我能跟你说句话吗?manbet手机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适时地跟着他去了书房。manbet手机版“拉特克利夫,”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学医。manbet手机版他的观点不容轻视。manbet手机版“是的,先生。”我回答道。大学申请表被修改了,没有进一步交换。manbet手机版我从不确定他认为我是一个好医生还是一个坏化学家,或者他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manbet手机版但我对自己很满意。manbet手机版尽管我不想去,但我提前一年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消磨。manbet手机版以前对爆炸动力学的痴迷又重新浮出水面,只不过伪装得更危险一些。manbet手机版我一直想擅长体育,而不是化学;manbet手机版灵虽强壮,肉体却软弱。manbet手机版现在,不管多么不可能,我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manbet手机版赛车运动。manbet手机版我在当地一家纺织公司的分析实验室工作,赚了足够的钱买一辆赛车卡丁车(不是卡丁车)。manbet手机版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manbet手机版在短时间内的加速确实令人兴奋。 It suited my basic interest in combustion. I learnt to ‘mechanic’ it (the most important bit) and drive tolerably, though not brilliantly well. It held prestige amongst a set of peers I admired. Though I never possessed a powerful motorcycle I had the gear to tune them for my friends. Mercifully for my poor parents, this period came to an effective end when I finally took up the place at University.
manbet手机版从这样的准备中可以预见,剑桥大学的医学并非完全成功。manbet手机版我就不详细讲了;manbet手机版只要说这不是大学的错,不是学院的错,也不是我导师的错就足够了。manbet手机版虽然我很容易就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潜力,但它离二冲程赛车发动机和相关文化太远了。manbet手机版虽然我交了好朋友,但我还是不能完全适应。manbet手机版可取之处是,六年课程中的三年临床课程通常在其他地方进行,通常是在伦敦。manbet手机版这提供了第二次机会。
manbet手机版圣巴塞洛缪医院的临床医学课程组织得很好,我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尤其是医学诊断的过程非常有趣。manbet手机版还有其他的好东西。manbet手机版我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妻子菲奥娜;manbet手机版菲奥娜也是医学院的学生。manbet手机版但是,从剑桥毕业后,我不想在考试中冒任何风险。manbet手机版我不太确定我想做什么,但我希望有选择的自由。manbet手机版在橄榄球比赛中仍然缺乏这些技能,成为家庭医生工作首选的最简单途径是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manbet手机版在这些考试中,大部分分数是通过多项选择题获得的。manbet手机版现在,大多数设置过这些考试的人都知道,只有某些类型的信息适合于练习。manbet手机版此外,即使题目没有正确地设置,也有可能看出考官试图设置什么问题并回答它。 I greatly enjoyed the medical course in a wider sense and flirted with a career in most every speciality covered in the curriculum, but I applied the above logic to the examinations with a brutality that still makes me blush. The result, in the main examination, was substantially more marks than any other student. Perhaps naively, I had not seen the difficulty that this might create. I was surprised by a summons to meet with the sub-dean. Most likely drawing on his experience as a former member of the Hospital Rugby Club, he could think of only one explanation; I had acquired copies of the examination papers in advance of the event. The interview has forever made me sympathetic to the cause of minority groups in police stations. In the end however, he was good enough to recognise that without a confession, the evidence was at best circumstantial and I was duly appointed to the House Physician post of my choice, on a ‘firm’ specialising in Gastroenterology and Nephrology.
manbet手机版在那段时间里,肾内科顾问医生拉里·贝克好心地建议我自己也当一名肾内科医生。manbet手机版就像兰开斯特皇家文法学校的校长一样,我不怀疑他的智慧,并相应地规划了我的职业生涯。manbet手机版其他人则更为谨慎:肾脏学是一门昂贵的专业,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资源不足。manbet手机版我清楚地记得,该专业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从那时(大约1980年)到2000年,只会有两个顾问职位空缺,所以我最好以某种方式让自己与众不同。manbet手机版第一个陈述被证明是不真实的;manbet手机版但第二件事却让人感到痛苦。manbet手机版作为一个忙碌的实习肾内科医生,没有真正的机会进行实验室研究。manbet手机版因此,作为区分的必要途径,我开始撰写医疗病例报告。manbet手机版在大多数科学圈子里,这都不会被视为一种有用的训练,更不用说一种杰出的训练了。manbet手机版后来,我变得善于重新安排我的出版物列表,所以我的科学发展的这一阶段不太明显。 Later still, I have come to see it as critical. What is important in embarking on a research career is selecting the question; once the question is clear, answers may follow. For most of us this is the joy of academic research; we are free to pick our questions. I moved from London to Oxford to complete my clinical training in Nephrology. The experience of surveying the patients of London postgraduate and Oxford hospitals for case histories from which something new might be securely deduced, was without doubt a key experience. It didn’t directly inform the question I eventually chose, but it taught me how to look for potentially soluble problems amidst a mass of insoluble distractions.
manbet手机版有一些错误的开始。manbet手机版我认为有可能了解导致肌红蛋白肾衰竭的肌红蛋白的物理化学性质,使用孤立的灌注肾脏。manbet手机版我从布莱恩·罗斯(Brian Ross)那里学会了肾脏灌注,他在manbet手机版汉斯·克雷布斯manbet手机版,但肌红蛋白即使在大量浓度对制备没有影响。manbet手机版然后,我认为有可能使用31磷核磁共振测量细胞能量学来理解为什么肾脏容易在休克中受伤,并加入了George Radda的实验室来研究这一点,但该方法的空间分辨率不够。manbet手机版我认为这可能会理解为什么肾脏在失血时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刺激红细胞生成的激素),而不是在血流减少时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manbet手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考虑到测量肾内血流动力学和氧通量的技术难度。manbet手机版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它们让我越来越接近“氧气感应”的问题。
manbet手机版我在肾内科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研究免疫学、遗传学或血压控制等截然不同的课题。manbet手机版我有点笨拙,不听话,这让我避开了这些话题,再加上从那个案例报告时代衍生出来的寻找可解决问题的经验,让我想到了这个问题。manbet手机版我认为,肾脏对血氧含量变化做出反应时,调节红细胞生成素产生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必须反映出一个可回答的重要问题,即潜在的“氧感知”过程的本质。manbet手机版并非所有人都同意;manbet手机版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肾脏患者中应用效果显著,为何担心其调控?manbet手机版但我确信会有一个答案,而且会很有趣。manbet手机版此外,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的鉴定为从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位点“向外”追踪到假定的氧传感器的转导途径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manbet手机版我已经完成了肾脏学的临床培训,需要做一个决定;manbet手机版我是否应该离开牛津大学,接受一个难得的机会,成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顾问肾病学家,一个据称有受保护的研究时间的人?manbet手机版还是留在牛津和朋友们在一起?manbet手机版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牛桥”的文化环境。manbet手机版来自医学部的David Weatherall和John Ledingham的个人保证支持,当我去威尔士一家医院看顾问职位时下了一场悲惨的大雨,在Wellcome Trust的面试中遇到了极大的好运,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确实不可能实现的雄心(作为一名工作的顾问肾病学家解决问题),作为一名资金充足的Wellcome Trust临床科学高级研究员,manbet手机版也许是有可能的。
manbet手机版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manbet手机版我对分子细胞生物学完全没有技术知识。manbet手机版当时,我并不是很担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无知程度一定让我的同事们感到惊讶。manbet手机版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早年当初级医生的经历。manbet手机版国民医疗服务处于长期的危机之中。manbet手机版我作为住院医生的那几年,恰逢卡拉汉政府的结束,英国经历了“不满的冬天”。manbet手机版“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罢工,没有任何工作。manbet手机版据我所知,在那些有权有势的高级职员眼中,医院内(有时也包括医院外)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由住院医生或注册主任(上一级)来解决。manbet手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以前从未想到,完全缺乏知识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manbet手机版但现在,就连我也明白了,有必要通过某种外部途径来获得分子细胞生物学方面的技能。manbet手机版我投资了一本本杰明写的卢因书manbet手机版基因三世manbet手机版去看朋友约翰·贝尔,他是我在伦敦国立神经疾病医院当内科医生时认识的。manbet手机版约翰很慷慨地给了我一个长凳的位置,让我在他拥挤的HLA免疫遗传学实验室里研究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调节。manbet手机版这很关键,给我下了套。manbet手机版所以,这是我对有抱负的临床科学家的建议,慢慢来,仔细看看周围,选择你的manbet手机版自己的manbet手机版问题,manbet手机版然后manbet手机版找一个朋友帮忙。
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我有很多朋友帮过我,最重要的是大卫·韦瑟尔,在我进入约翰的实验室后,他在他新成立的分子医学研究所给了我一些自己的实验室空间。manbet手机版在邻近的海湾里有理查德·琼斯,我非常感谢他。manbet手机版理查德教了我很多我们在工作初期使用的基因调节技术。manbet手机版卡罗尔·博蒙特(Carole Beaumont,与理查德一起休假)教我组织培养。manbet手机版剑桥大学的马丁·约翰逊(Martin Johnson)为我制造了转基因小鼠,试图通过在促红细胞生成素位点表达T抗原来获得肾脏中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细胞。manbet手机版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当地,人们对这个项目越来越有信心;manbet手机版一系列优秀的实习肾内科医生,Tan Chorh Chuan, Chris Pugh, Patrick Maxwell, John Firth, Jonathan glleadle来了,或者被我引导着。manbet手机版Ben Ebert以美国罗德学者的身份加入实验室;manbet手机版Masaya Nagao从日本加入我们。manbet手机版所有人都在冒险,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记录。
manbet手机版那是一段繁忙的时光。manbet手机版菲奥娜也从伦敦搬到了牛津。manbet手机版我们在1983年结婚,那时她是一名实习麻醉师。manbet手机版在我完成我自己的肾脏学培训,决定要做什么,然后建立实验室的关键时期,她生了我们的四个孩子:安娜,爱丽丝,罗伯特和大卫。manbet手机版我偶尔会带年幼的孩子们来实验室,用干冰逗他们玩,这是我童年时代关于炸药的另一个主题。manbet手机版我把周末实验与家庭散步和海边旅行结合起来,总体上认为我处理得很好。manbet手机版只有回想起来,我才发现菲奥娜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她几乎是独自一人管理自己的训练、孩子和家庭。manbet手机版我很感激她的坚韧。
manbet手机版通过药物干预促红细胞生成素对低氧刺激的反应来理解氧感知过程的本质,已经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manbet手机版但是,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的鉴定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manbet手机版已经证实,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是通过转录调控的。manbet手机版因此,我们认为,从基因出发,应该有可能在基因位点上定义氧调控的控制序列,然后通过转录和信号转导途径来分析假定的氧传感器。manbet手机版然而,尽管我们在实验室里有很多天赋和热情,但我们都没有接受过生化训练。manbet手机版除了通过基因转移鉴定氧调控控制序列之外,解剖这些途径最明显的方法是生物化学。manbet手机版正如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所解释的,基于基因的新的分子方法为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打开了细胞生物学的研究问题,我们进入实验室时没有接受过生物化学方面的培训,但这是有局限性的。manbet手机版即使是大卫·韦瑟罗尔和他的分子医学研究所创造的环境也无法解决这个缺陷。manbet手机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基因方法。manbet手机版其中一个意外地直接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突破。
manbet手机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促红细胞生成素对血氧降低的异常敏感性反映了一种高度特化的氧传感器的功能,这种传感器是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细胞本身特有的。manbet手机版红细胞生成素由肾脏细胞产生,少量由肝脏细胞产生。manbet手机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从促红细胞生成素- T抗原转基因小鼠的肾脏中培养这些细胞,但没有成功。manbet手机版最后,哈佛大学的富兰克林·布恩(Franklin Bunn)及其同事发现,肝脏细胞系在缺氧时产生了促红细胞生成素,这开启了分子方法的研究之路。manbet手机版我们和其他人使用这些细胞作为载体,在促红细胞生成素位点上定义氧传感控制序列。manbet手机版但接下来是我的生化问题;manbet手机版如何到达目标,在上游的氧气感应装置。manbet手机版该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学家戴夫·西蒙斯(Dave Simmons)成功地在Cos7细胞中使用“表达克隆”来识别表面受体和细胞粘附分子。manbet手机版我想我可以利用这项技术通过基因转移来识别氧敏感途径的上游成分。manbet手机版这将是从Franklin Bunn的氧敏感肝癌细胞到Cos7细胞,我认为Cos7细胞本质上不是氧敏感的,因为它们不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 To my great surprise, control experiments – designed to check the absence of oxygen sensitivity prior to gene transfer – clearly showed the same oxygen sensitivity of those control sequences isolated from the erythropoietin locus, in Cos7 cells.
manbet手机版这当然取消了我的实验计划,但却改变了我科学生活中的一切。manbet手机版这是第一个证明人类氧感知系统广泛存在的证据,而且明显超出了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范围。manbet手机版这意味着很明显,在不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细胞中一定有其他的靶点,这些细胞也受到氧气水平的高度敏感调节。manbet手机版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第一个:编码特定同工型糖酵解基因的酶,这些基因在癌症中也被上调,将我们与癌症代谢和肿瘤学社区联系起来。manbet手机版尽管这项工作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最初的出版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确信我们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manbet手机版然而,研究这一问题的一小群科学家所表现出的巨大兴奋与整个科学界对此产生的兴趣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manbet手机版它仍然影响着我对年轻科学家的建议;manbet手机版当你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尽量忽略你周围人的兴趣和偏见,他们可能会远远落后于你。manbet手机版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对HIF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一种结合氧调控序列的转录因子,由Gregg Semenza发现)有反应的新途径,该领域稳步增长。manbet手机版然而,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对HIF转录级联的程度感到惊讶,以及对缺氧(低组织氧水平)的如此多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Many of the new responses to hypoxia were fascinating in their own right, but our intention had always been to work our way upstream to the oxygen sensing mechanism itself and our attention shifted back.
manbet手机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大卫分子医学研究所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团队,我们充分利用了它所提供的一切。manbet手机版整层楼的一半被用作研究所的咖啡室。manbet手机版大卫显然对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这个备受推崇的设施印象深刻。manbet手机版咖啡是提前做好的,不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在设计和间距完全正确的扶手椅上喝,以支持谈话。manbet手机版房间里铺着地毯。manbet手机版对于那些考虑制度设计的人来说,这一点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manbet手机版我们坐在那里,与任何愿意倾听和推测(主要是徒劳的)氧气感知机制可能是什么,以及(更有成效的)我们可能用来定义它的实验策略的人坐在一起。manbet手机版对于每一位参观者,我都从解决氧气传感问题的潜力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工作,这也是我的问题。manbet手机版我们试图利用一系列的基因转移和表达克隆方法,我们检查了模式生物的路径保护,希望在苍蝇,线虫,甚至酵母中利用遗传方法。manbet手机版乔治·斯塔克(George Stark)利用体细胞遗传学解剖干扰素反应途径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Morwenna Wood and Emma Vaux, two highly competent trainee Nephrologists, spent vast amounts of time engineering 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 to express hypoxia inducible transgenes encoding cell surface markers, and then selecting mutants with defective responses to hypoxia. To their enormous credit, they did isolate valuable mutants, but it proved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defective genes beyond those encoding components such as HIF that we already knew about.
manbet手机版最终,是遗传和生物化学方法的混合,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找到了解决方案。manbet手机版每一次进步都是递增的,这是编辑们在退稿时最喜欢用的词。manbet手机版定义了HIF中介导复合物氧敏感性的调控结构域,展示了这些结构域与von Hippel-Lindau蛋白(pVHL)的物理联系,展示了pVHL作为一种降解HIF的泛素连接酶的功能,发现了脯氨酸羟化作为调控pVHL与HIF氧调节关联的机制,证明催化HIF脯氨酸羟化的酶属于2-羟戊二酸依赖的双加氧酶家族,manbet手机版鉴定的实际酶及其氧敏感性,都是manbet手机版增量manbet手机版步骤。manbet手机版我是因我们对这项工作的贡献而有幸被召到斯德哥尔摩的人之一,但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工作对所有这些渐进进展的及时发表作出了贡献,并从中得到了启发。
manbet手机版最后的步骤,包括鉴定实际的氧敏感2-羟戊二酸依赖双加氧酶,催化HIF的脯氨酸羟化,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克里斯托弗·斯科菲尔德(Christopher Schofield)共同完成的,我的实验室继续与他进行着良好的合作。manbet手机版克里斯(牛津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带来了我所缺乏的生物化学视角。manbet手机版但最初的合作工作并不是大规模的生化净化,我之前曾设想过在项目的某个阶段是必要的。manbet手机版相反,基于他早期对依赖于2-羟戊二酸的双加氧酶和相关酶的结构分析,克里斯能够预测可能编码推定的氧敏感脯氨酸羟化酶的基因。manbet手机版与此同时,我们早期在韦瑟罗尔咖啡馆里进行的一次探索性冒险,涉及到在manbet手机版Caenorrhabditis线虫manbet手机版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会产生对抗这种蛋白质的抗体。manbet手机版这使我们能够评估突变体对缺氧对HIF蛋白水解调节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突变体显示出异常。manbet手机版Chris预测的2-羟戊二酸依赖双加氧酶之一在突变体库中被表达manbet手机版秀丽隐杆线虫manbet手机版这些都是由线虫遗传学社区提供的漂亮的分类和有效的。manbet手机版通过WormBase对携带相关基因突变等位基因的蠕虫进行鉴定并进行排序。
manbet手机版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3月的一个早晨;manbet手机版安迪·爱泼斯坦,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冲进我的办公室,大声说,‘这是你的基因,manbet手机版Egl9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突变体的三个不同等位基因manbet手机版Egl9manbet手机版基因,先前由诺贝尔奖获得者Bob Horvitz在其卵子排出缺陷的机械不可知基础上描述,都显示出它们的HIF上调,与氧水平无关,正如预测的一个有缺陷的酶,其氧依赖催化脯氨酸羟化在生理上被用于信号氧水平。manbet手机版我们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并确定了三个人类同源体。manbet手机版乔纳森·格莱德(Jonathan Gleadle)是加入实验室的实习肾内科医生之一,他做了一些定义hif靶基因的早期工作,在完成临床培训后回到了小组。manbet手机版乔纳森发现了人类的同类manbet手机版Egl9manbet手机版基于高度保守的催化结构域,并将他们的产品称为PHD(脯氨酸羟化酶结构域)酶。manbet手机版这些发现完成了我作为一名年轻肾病学家的旅程,从促红细胞生成素到氧气。manbet手机版旅程的高潮是激动人心的,非常激动人心;manbet手机版那些我容易忘记的低谷。manbet手机版这种体验让人上瘾,我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尤里卡”的发现时刻。
manbet手机版虽然这项工作为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但保护氧气稳态显然更加复杂。manbet手机版严重的缺氧在几分钟内是致命的,必须在比我们迄今为止所揭示的转录途径所介导的更短或更长的时间内维持氧气稳态。manbet手机版例如,颈动脉体控制呼吸的氧敏感信号,这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的工作的一部分狗万世界杯manbet手机版Corneille海曼manbet手机版1939年,仍然没有在分子水平上被理解。manbet手机版实验室的工作在这些和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在生理学的氧稳态。manbet手机版虽然我们最初惊讶地发现HIF系统一般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起作用,而不局限于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细胞,但我们随后惊讶地发现它显然局限于动物生命,在非后生动物物种中没有明显的HIF同源物。manbet手机版现在很清楚的是,所有四个真核生物王国的物种都部署了蛋白质酶氧化和蛋白质降解,以信号细胞中的氧气水平。manbet手机版然而,氧化是不同类型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耦合到信号系统,提出了关于这些系统的起源、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是否也在人类氧感测中起作用的问题。manbet手机版我也开始对癌症感兴趣,特别是非常广泛的相互联系的生理通路的致癌“切换”的影响,例如在肾癌中pVHL泛素连接酶失活和HIF系统非生理激活时发生的情况。manbet手机版我想,这种范式,特别是发展中的癌症“适应”致癌激活途径的不良成分的机制,对于理解这种疾病将是重要的。manbet手机版由于这些原因,在与我共事多年的忠诚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实验室一如既往地活跃,或至少一如既往地充满希望,而我也一如既往地沉迷于发现过程。
manbet手机版但也有新的经历。manbet手机版我曾与大大小小的公司合作,开发用于治疗贫血和其他缺血/缺氧疾病的HIF羟化酶抑制剂。manbet手机版对于一个习惯于几乎完全控制实验研究项目的实验科学家来说,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manbet手机版看到这项工作朝着药物的方向发展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尽管无法控制这种情况有些令人担忧。manbet手机版但也有同样的不可预测性。manbet手机版鉴于该领域开始于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调控,因此,作为HIF羟化酶抑制剂开发的2-羟葡二酸类似物将诱导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产生并纠正促红细胞生成素缺乏症的贫血也就不足为奇了。manbet手机版但考虑到HIF转录级联的程度变得明显,我不认为科学界会预测到,如果没有对缺氧的其他反应的严重失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目前的临床经验所显示的那样。manbet手机版我学会了尊重那些承担药物开发过程中固有风险的人。
manbet手机版2003年,我被邀请担任临床医学系的系主任。manbet手机版约翰·贝尔已经接替大卫·韦瑟罗尔坐上了这个位子,现在正(和大卫一样)搬到皇家主席的位置上。manbet手机版我犹豫了,因为我很清楚大学管理不是一个天生的工作。manbet手机版但是这个部门很有趣。manbet手机版在大卫和约翰的成功任期内,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学院系的标准,更像一个小型大学的规模,研究预算将在英国大学联盟中脱颖而出。manbet手机版它过去和现在(按照名称)是一个系manbet手机版临床manbet手机版医学涵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学科,包括结构生物学、大规模人类遗传学、临床试验、流行病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热带医学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临床医学教学。manbet手机版期望高级教授工作人员为急性医学轮值表作出贡献,并在这方面教授医科学生。manbet手机版凭借我在临床肾脏病学方面的训练,以及在我刚刚描述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肾脏病学和急性医学方面的持续实践,我实际上可以做到这一点。manbet手机版我的感觉是,这让一些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其他医疗和护理人员略感意外;manbet手机版这确实让我在实验室的一些博士后感到恐惧。manbet手机版他们认为这种“高压”药物只能由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穿着外科手术服的高度专业、非常好看的工作人员来执行。manbet手机版我从来没有完全确定,他们觉得自己缺乏哪些特质。manbet手机版然而,临床医学只是经历的一部分。manbet手机版该部在所有领域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在热带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作。manbet手机版这种规模的学术管理是一个挑战,总的来说,我学会了不去尝试。 I learned a lot about people, particularly creative people. In the Department, as in the laboratory,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s (to me) turned out to have their value. I learned tolerance and firmly believe that science is, or should be, one of the great unifying forces in a world of diversity. Of course, a persistent problem was balancing Departmental matters with the running of the laboratory, and I’m grateful to many on both sides of that equation who ensured at least a modicum of success. But I avoided further progression in academic management, and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in the position, looked for opportunities that might give me more time in the laboratory and new scientific horizons.
manbet手机版因此,2015年,manbet手机版保罗的护士manbet手机版来找我,想在一家即将开张的公司找个职位manbet手机版弗朗西斯·克里克manbet手机版研究所,以发展其与临床从业者和临床医学的接口。manbet手机版在这里,我想我不同寻常的医学经验可能会有用。manbet手机版新的科学视野出现了。manbet手机版我刚才所描述的旅程的关键点是,研究问题的选择至关重要。manbet手机版把临床医生带到像克里克这样的大型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目的是,他们会提出新的问题,不一定是临床问题,只是不同的问题。manbet手机版作为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的一员,我把克里克的职位与我在牛津大学(Oxford)的实验室各占一半的比例结合起来,觉得事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至少在10月的一个上午之前是这样。
manbet手机版在讨论氧气传感工作的优点或其他方面时,我听说过诺贝尔奖,但那天早上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manbet手机版在和来自芬兰的同事一起写一份拨款申请时,我遇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危机点,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manbet手机版在疯狂的活动中,我几乎忘记了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意义。manbet手机版但我的私人助理凯瑟琳不会忘事。manbet手机版是凯瑟琳把我从周一上午的实验室会议中拉出来接托马斯·帕尔曼(Thomas Perlmann)的电话,当我回来结束会议时,她把我的浓咖啡换成了一杯镇静的茶。manbet手机版随后,实验室里一整天都喝了大量的香槟,正如电视观众所观察到的那样,安全标准变得松懈了。manbet手机版许多人都讲述了一夜之间被赋予无所不知的超现实经历。manbet手机版就连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也认为,在短时间内,我对一些事情可能会有有用的看法。manbet手机版但斯德哥尔摩的经验值得重申。
manbet手机版把诺贝尔周变成一个庆祝活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成为一个快乐的时刻,这真的很了不起。manbet手机版每一项活动都办得尽善尽美,每一个麦克风都调得很准,所有的电子投影都完美无缺。manbet手机版国王是威严的,王后是优雅的,公主们是美丽的。manbet手机版在Grand酒店吃早餐Hôtel,俯瞰斯德哥尔摩ström,是这个星球上最愉快的体验之一。manbet手机版本周繁忙的日程安排由我们的attaché简·维奥尔有效地管理。manbet手机版甚至我的赛车梦想似乎也得到了考虑;manbet手机版我们的车手博·克拉力赛冠军。manbet手机版只有一个小问题。manbet手机版我们全家带着刚出生的孙女,她的母亲(安娜)和父亲(鲁珀特)匆匆拿到了护照,来到了斯德哥尔摩。manbet手机版在最紧张的时刻,为婚礼穿衣服,结果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五个小时的宴会上容纳婴儿。 My wife Fiona took the matter seriously. After 37 years of marriage, I did not doubt the outcome. I carried on wrestling with buttons on the formal attire. I think Miss Elizabeth Merryn Everleigh is youngest to attend that magnificent Nobel banquet, safely tucked away under that very grand staircase through which we had entered the Hall. What a day.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传记是在获奖时撰写的,后来以丛书形式出版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这些信息有时会以获奖者提交的附录进行更新。
manbet手机版看看2022年诺贝尔奖的公告吧
manbet手机版即将到来的
manbet手机版观看直播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