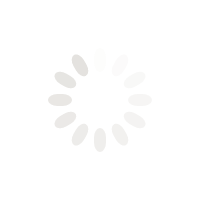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d·卡尔顿Gajdusek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我对科学的兴趣在我上学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是个五岁的男孩,和我母亲的昆虫学家姐姐坦特·艾琳(Tante Irene)漫步在花园、田野和树林中,翻动岩石,试图找出以前隐藏的生命中有多少不同的动植物物种。manbet手机版我们切开虫瘿,寻找长出肿瘤的昆虫,在室内孵化的小树枝上收集奇怪的、坚硬的、黏糊糊的东西,这些小螳螂在窗帘里孵出,我们还发现有长长的产卵器的黄蜂,它们把卵产在蛀木甲虫的幼虫里。manbet手机版在培养皿中,我们看到一些食叶昆虫死于杀虫剂中毒,而另一些则存活了下来。在令人兴奋的旅行中,我们参观了位于我家乡纽约州杨克斯的博伊斯·汤普森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和实验温室。我的姑妈艾琳·多布罗斯基在那里工作,研究20世纪20年代叶跳虫细胞中的病毒包体。
manbet手机版我对科学的兴趣在我上学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是个五岁的男孩,和我母亲的昆虫学家姐姐坦特·艾琳(Tante Irene)漫步在花园、田野和树林中,翻动岩石,试图找出以前隐藏的生命中有多少不同的动植物物种。manbet手机版我们切开虫瘿,寻找长出肿瘤的昆虫,在室内孵化的小树枝上收集奇怪的、坚硬的、黏糊糊的东西,这些小螳螂在窗帘里孵出,我们还发现有长长的产卵器的黄蜂,它们把卵产在蛀木甲虫的幼虫里。manbet手机版在培养皿中,我们看到一些食叶昆虫死于杀虫剂中毒,而另一些则存活了下来。在令人兴奋的旅行中,我们参观了位于我家乡纽约州杨克斯的博伊斯·汤普森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和实验温室。我的姑妈艾琳·多布罗斯基在那里工作,研究20世纪20年代叶跳虫细胞中的病毒包体。
manbet手机版在我上学的头几年,我和老师有过争执,因为他们把杀虫罐带到学校,上面正确地标着“毒药:氰化钾”。manbet手机版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在博伊斯·汤普森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遇到了数学家和物理化学家威廉·j·约登博士安静、有趣、警觉和指导的眼睛,他喜欢让我玩他的手摇柄台式计算器,他的圆形或圆柱形计算尺,还有晶格结构模型,manbet手机版在他的实验室长凳上,他教我制备胶体金溶液,时间显色反应和制造硫氰酸汞致蛇片。manbet手机版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想成为像姑姑和安静的数学家导师那样的科学家。manbet手机版我和我的弟弟罗伯特(Robert,他现在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一样,完全拒绝了父亲和外祖父在商业上的兴趣,正是商业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manbet手机版我的生活和观点受到讲多种语言的东欧移民社区的极大影响,他们毗邻而又不情愿地交织在一起,住在地毯、电梯、铜线制造和制糖城市扬克斯(Yonkers),就在纽约大都市哈德逊河(Hudson River)的上游,课本上记载着17世纪荷兰皇家将印第安土地授予约翰·赫尔(Johng Heer,也就是扬克斯)阿德里安·范德东克(Adrian van der Donck)的历史。manbet手机版客厅里的钢琴旁,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吉卜赛人在演奏manbet手机版民间manbet手机版而且manbet手机版halgatosmanbet手机版在我父亲肉铺旁边的空铺子里露营,用多种语言的大声交谈,很少是英语,厨房里弥漫着哈布斯堡式菜肴的香味,让我对美国产生了正统和乐观的看法,认为它是一块充满变化和可能性的土地,我从未失去过这种看法。manbet手机版在我们那几乎是乡村的山顶住宅下面——我们的家族已经“崛起”——聚集着工厂、教堂、商店和两到四个移民工厂工人和商人的家庭住宅,这些房屋位于几乎被摧毁的尼珀汉河(Nepperhan)和印第安人命名的塔卡霍河(Tuckahoe)的山谷中。manbet手机版在这片空地上,有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还有一个为工厂工人设立的长老会。manbet手机版(这个东欧人的令人兴奋的聚集地后来被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所取代,后来又被美国黑人所取代,所有这些人都同样在“融化”。)
manbet手机版我的父亲卡尔·加伊杜塞克是一个斯洛伐克农场男孩,来自塞尼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十几岁就离开家,独自一人,不会说英语,移民到美国,在扬克斯的移民社区当了一名屠夫。在扬克斯,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奥蒂莉亚·多布罗茨基,并与她结婚。manbet手机版她的父母也是年轻时从匈牙利德布勒森移民到美国的,两人都是独自一人。manbet手机版在我父亲这方面,我们是一个农民和商人的家庭,我哥哥和我自己从来没有对这些职业感兴趣,但我父亲喜欢大笑和下流的娱乐,对生活的热爱,对工作和娱乐、音乐、歌曲、舞蹈和食物,尤其是谈话;manbet手机版我们强烈的影响。manbet手机版在我母亲这边,有四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第一代美国兄弟姐妹较为严肃的学术和美学抱负,以及对幻想和探索、对经典和文化、自然、培养和过程的英雄般的兴趣。manbet手机版由于母亲对文学和民间传说有着不可抑制的兴趣,我和弟弟在学会阅读之前,就听着荷马、赫西奥德、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和维吉尔的作品长大。
manbet手机版1923年9月9日,我出生在我们仍然拥有的那栋房子里,当时我的外祖父母和我母亲最小的妹妹住在一起。manbet手机版我哥哥19个月后来到了这里。manbet手机版他和我一起成长;manbet手机版我在数学和科学上每迈进一步,他就在诗歌、音乐和其他艺术上迈进一步。manbet手机版1930年,我们去欧洲看望亲戚,大部分是我父亲大家庭的亲戚,他在20年前就抛弃了这个大家庭。manbet手机版我和弟弟被留在父亲的出生地,与他的老父亲和剩下的庞大家庭(乡绅生了大约25个孩子)一起住了几个月,而我们的父母则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旅游。
manbet手机版在美国,我早年的求学时光是非常快乐的:我喜欢上学,经常有迷人的全家到哈德逊河谷远足。manbet手机版我的Tante Irene正在研究菲律宾和东南亚的经济昆虫学问题,异国的文物和自然历史标本,尤其是穿着蜡染一样图案的美丽的巨型叶蝉,让我着迷。manbet手机版从东方回来后,她带着我进行了更广泛的旅行,去收集昆虫,去观看十七年蝉的出现,去参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会议。manbet手机版我很早就成为了纽约市博物馆的habitué常客,在五年级课后的下午,我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参加埃及学课程,周末和晚上去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听昆虫学、地质学和植物学的讲座。
manbet手机版今天,我和我那由新几内亚和密克罗尼西亚收养的儿子组成的大家庭,在我们经常去纽约的时候,仍然住在我五十三年前出生的老家。manbet手机版在这里,孩子们最近在安装新的阁楼隔热材料时,发现了多瑙河以东城镇和世纪之交纽约市拍摄的家庭照片,以及曾经属于我母亲、她的兄弟姐妹、我哥哥和我自己的学校笔记本。manbet手机版也是在这个家,我们埋葬了我的外祖父母,还有我的父母。manbet手机版在我的异教徒母亲去世的那一天,由于斯洛伐克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都被命名为“圣三位一体”,两者不可避免地相距很近,导致了混乱,导致她与错误教派的神职人员一起埋葬,而我试图缓和这一情况,请殡仪主任把牧师叫来,他们是我不敬的父亲的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亲戚,在他早些时候的葬礼上,斯洛伐克牧师拒绝主持。
manbet手机版青春期前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manbet手机版北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和manbet手机版西格丽德温manbet手机版这些都是我自己早期读过的作品。manbet手机版我热情地阅读了三部传记作品,它们一定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né瓦莱里-拉多为他的岳父路易·巴斯德写的传记;manbet手机版夏娃·居里的母亲传记,manbet手机版居里夫人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以及保罗·德·克鲁夫的《微生物猎人》。manbet手机版然后,我在通往我的阁楼化学实验室的台阶上用模板刻上了德克鲁夫挑选的12位微生物学家的名字,这些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manbet手机版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为什么我打算专注于化学、物理和数学,而不是经典生物学,为将来的医学生涯做准备。manbet手机版约登博士成功地让我明白,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是未来生物学的基础。
manbet手机版13岁到16岁的夏天,我经常在博伊斯·汤普森实验室工作。manbet手机版在约翰·亚瑟博士的指导下,我合成并表征了一系列卤代芳氧乙酸,其中许多是以前未合成的。manbet手机版我从这些化合物中提取出的一系列新化合物没有产生预期的杀蝇能力,但当几年后对它们的杀菌能力进行测试时,我的一种新化合物2,4-二氯苯氧乙酸成为了商业上的除草剂;manbet手机版研究所的专利权是根据我少年时代的实验室笔记本获得的,那是我唯一的商业冒险。
manbet手机版我在博伊斯·汤普森中学的经历,尤其是在约登中学的经历,使我转向了罗切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在那里,我希望实现我的计划,即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为从事医学研究职业做准备。这一计划是我在少年时代根据姑姑和约登的阅读和教导制定的。
manbet手机版从1940年到1943年,我在罗切斯特大学维克托·韦斯科普夫的物理专业学习;manbet手机版科特·斯特恩,唐·查尔斯,大卫·戈达德,吉姆·古德温,生物学;manbet手机版数学方面的弗拉基米尔·赛德尔;manbet手机版以及化学方面的拉尔夫·赫尔姆坎普。manbet手机版1941年夏天,我受到了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维克托·汉堡的海洋胚胎学课程的启发。manbet手机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学会了热爱登山、徒步旅行、划独木舟和露营,并像热爱科学一样充满激情。
manbet手机版19到22岁的时候,我还在哈佛医学院读书,在蛋白质物理化学实验室和约翰·t·埃德萨尔一起工作,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和詹姆斯·l·甘伯一起工作,在他的电解质平衡实验室工作。manbet手机版从那以后,在25岁和26岁的时候,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manbet手机版莱纳斯鲍林manbet手机版还有约翰·柯克伍德,他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manbet手机版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乔治小吏manbet手机版、沃尔特·泽克迈斯特和詹姆斯·邦纳。manbet手机版正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同行们——博士后同事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冈瑟·斯坦特、杰克·邓尼茨、埃利·沃尔曼、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特、大卫·苏梅克、约翰·坎、哈维·伊塔诺、阿吉·波尔、奥勒·马洛埃、特德·哈罗德、约翰·芬查姆、莱因哈特·鲁格、阿诺德·马祖尔、阿尔·里奇和其他人)——对我的智力发展、目标和创造性生活中对质量的欣赏以及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anbet手机版这是加州理工学院的“黄金时代”,许多在不同学科工作的亲密朋友,以及我们的导师,在科学领域一直相互激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30年里,我们是长久的私人朋友。manbet手机版与这群学生一起讨论莱纳斯·鲍林、约翰·柯克伍德、马克斯·Delbrück和乔治·比德尔,我花了许多个日夜在实验室和艺术学院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就去西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沙漠和山区露营和徒步旅行进行了更长时间的交流。manbet手机版马克斯和曼尼Delbrück经常在他们家招待我们,也是我们许多探险活动的主要组织者。manbet手机版在加州理工学院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结交了一群朋友,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们与我临床和实验室调查的专业老师一起组成了陪审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最尊重他们的判断。
manbet手机版我没有想到我对临床儿科的着迷。manbet手机版儿童让我着迷,他们的医疗问题(由于各种不成熟、成长和成熟的变量对困扰他们的每一个临床实体的影响而复杂化)似乎比成人医学提供了更多的挑战。manbet手机版在医学院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围墙内生活和工作。manbet手机版此后,我开始了临床儿科学的研究生专业培训,并通过专业委员会的资格,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内科和外科医生学院的Michael Heidelberger的实验室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和manbet手机版约翰·恩德斯manbet手机版哈佛的研究生课程manbet手机版我从未放弃过我的临床兴趣,特别是在儿科和神经学方面,这是由一群鼓舞人心的床边老师培养起来的:哈佛大学的马克·阿尔特舒勒、路易斯·k·戴蒙德、威廉·拉德、弗兰克·英格拉姆、西德尼·加里斯和卡农·伊莱;manbet手机版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婴儿医院的Rustin McIntosh, Hattie Alexander, Dorothy Anderson和Richard Day;manbet手机版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Katie Dodd Ashley Weech Joe Warkany和Sam Rappaport,以及巴尔的摩的Ted Woodward。
manbet手机版1951年,我应征入伍,从哈佛大学约翰·恩德斯的实验室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服务研究生院,作为一名年轻的病毒学研究家,在那里我被约瑟夫·斯莫德尔博士召去。manbet手机版我发现,他对我过于雄心勃勃的项目和古怪的计划报以严厉和适度的鼓励,教我更多的是进行实验室和实地研究的方法,以及展示科学成果的方法,而不是任何进一步的理论上层建筑,他认为我已经拥有了。
manbet手机版1952年至1953年,我曾在德黑兰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狂犬病、鼠疫、虫媒病毒感染、坏血病和其他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流行病研究。从他和德黑兰巴斯德研究所的马塞尔·巴尔塔扎德那里,我了解到对外来和孤立人群的流行病学问题进行紧急机会调查所带来的兴奋和挑战。manbet手机版我对原始种群分离的医学问题的探索带我去了兴都库什山脉的山谷、南美洲的丛林、新不列颠的海岸和内陆山脉、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马来西亚的沼泽和高山谷,但总是有一个安静沉思和令人兴奋的实验室研究的基地,与约翰·恩德斯在波士顿,乔·斯莫德尔在华盛顿,和manbet手机版弗兰克·伯内特manbet手机版在墨尔本。manbet手机版我感谢这些老师,感谢他们的引导和启发,感谢他们多年来的鼓励和友谊。
manbet手机版我还感谢乔·斯莫德尔进一步的赞助和鼓励,并承认我在卓有成效的研究方面的科学潜力,这使他在几年后为我创造了一个当时独一无二的职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疾病和失明研究所的美国访问科学家,由理查德·马斯兰德博士领导,manbet手机版在那里,我可以培养我的各种兴趣,在一个自称为“原始文化中儿童生长发育和疾病模式研究”的项目中。manbet手机版我们的慢、潜伏和温和病毒感染实验室是在对库鲁病这一“疾病模式”的阐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医学领域。manbet手机版大约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享受着我们在世界偏远地区进行多样化研究的基地和避风港,与一小群学生和同事以及许多访问同事一起,他们组成了我们努力的强大团队。manbet手机版在这里,玛丽昂·珀姆斯、乔·吉布斯、保罗·布朗、文·齐加斯、迈克尔·阿尔珀斯、大卫·阿舍和南希·罗杰斯与我分享了近二十年来的这些冒险经历。
manbet手机版我少年时代的阅读,首先是荷马、维吉尔和普鲁塔克的作品,我们的匈牙利古典浪漫主义母亲培养了我们。在我的诗人哥哥的鼓动下,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太热心的科学家兼医生,更彻底地回到了古典文学中,也回到了欧洲作家和哲学家的现代文学中,我在大学时代太专注于数学和科学,错过了这些。manbet手机版这次阅读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manbet手机版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manbet手机版蒙田,波德莱尔,兰波,瓦莱里和manbet手机版纪德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叶芝和劳伦斯;manbet手机版坡、惠特曼和梅尔维尔;manbet手机版易卜生;manbet手机版歌德,席勒,康德,尼采,卡夫卡和manbet手机版曼恩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萨阿迪和哈菲兹。
manbet手机版1954年,我飞往澳大利亚,与弗兰克·伯内特(Frank Burnet)一起在墨尔本的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担任访问研究员。在那里,我在免疫学和病毒学的实验室工作期间,开始了针对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口的儿童发育和疾病模式的研究。
manbet手机版在18卷约5000页的关于我对原始文化的探索和探险的个人日记中,自1957年我第一次看到库鲁病以来,在文森特·齐加斯的指导下,我对自己和我的工作讲述的比一个人一生应该讲的多得多……我不知道我怎么能précis在这里。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传记是在获奖时写的,后来以丛书的形式出版manbet手机版Les大奖赛诺贝尔/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这些信息有时会随获奖者提交的附录而更新。
manbet手机版D. Carleton Gajdusek于2008年12月12日去世。
manbet手机版观看2022年诺贝尔奖公告
manbet手机版即将到来的
manbet手机版观看公告的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