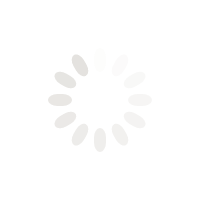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萨尔瓦多卡西莫多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
manbet手机版英语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1959年12月11日
manbet手机版诗人与政治家
manbet手机版“永远找不到白天的黑夜太长了”。manbet手机版这是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说的话,它们帮助我们定义了诗人的状况。manbet手机版起初,在诗人看来,读者在孤独中是一个童年朋友的脸和手势的形象,也许是一个更敏感的朋友,他在独自阅读方面经验丰富,但在评估对世界的假定的描述或错误的描述方面有点缺乏自信。manbet手机版这种表现是用与科学无关的严格的诗意手段和声音预先确定的词语来尝试的。
manbet手机版对诗人来说,对一个人的精确的诗歌复制是对地球的否定,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他最大的愿望是对许多人说话,用和谐的诗歌来团结他们,讲述心灵或事物的真理。manbet手机版天真有时是一种敏锐的品质,能最大限度地表现理智。manbet手机版而诗人的朋友的天真,他辩证地要求最初的诗歌节奏有一个逻辑形式,将保持一个固定的参考点,一个使诗人能够构建半个抛物线的焦点。manbet手机版诗人的其他读者是古代诗人,他们站在一个坚不可摧的距离上看着新写的书页。manbet手机版他们的诗歌形式是永恒的,很难创造出新的形式来接近他们。
manbet手机版故事或小说的作者锁定人物并模仿他们;manbet手机版他穷尽了他笔下人物的各种可能性。manbet手机版诗人独自一人,在他自己朦胧的领域里拥有无限的目标,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无动于衷,还是应该满怀希望。manbet手机版后来,这张脸会倍增;manbet手机版这些姿态会变成赞同或反对的意见。manbet手机版这发生在第一首诗出版的时候。manbet手机版正如诗人所预料的那样,警钟现在敲响了,因为——必须再次强调——诗人的诞生总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威胁,因为他试图突破文学种姓的圈子,到达中心。
manbet手机版他现在有了一群奇怪的公众,开始与他们保持沉默和敌对的关系:批评家、乡绅教授和文人。manbet手机版在诗人的青年时代,这些人大都摧毁了他的玄学,纠正了他的形象。manbet手机版他们是抽象的评判者,根据一种冷漠的、诗意的标准来修改“错误的”诗歌。
manbet手机版诗也是诗人的肉体自我,不可能把诗人和他的诗分开。manbet手机版然而,我不愿沉浸在自传中谈论我自己的国家,众所周知,每个世纪都充满了乔瓦尼·德拉·卡萨斯,也就是说,充满了韵律整齐和充分发展的灵巧的文人。manbet手机版这些传统的大祭司有千里眼和想象力。manbet手机版此外,他们痴迷于有关世界必将毁灭的寓言。manbet手机版他们不容忍编年史,只容忍理想的人物和态度。manbet手机版对他们来说,诗歌的历史就是幽灵的画廊。manbet手机版如果考虑到我自己的第一次诗歌实验是在独裁统治时期开始的,并且标志着赫尔墨斯运动的起源,即使是辩论也有一定的道理。
manbet手机版从我193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到第二、第三和第四本书(出版于1940年的希腊歌词译本),我成功地透过政治迷雾和学术界对背离标准古典作品的苛刻诗歌的厌恶,看到了一个由谦逊或雄心勃勃的读者组成的分层公众。manbet手机版的manbet手机版Lirici Grecimanbet手机版(1940年)[希腊歌词]在当时的文学世代中进入了新鲜和新鲜的阶段;manbet手机版他们在整个欧洲开启了更真实的经典阅读。manbet手机版我知道许多年轻人在他们的情书中引用了我的歌词;manbet手机版还有一些是政治犯写在监狱墙上的。manbet手机版多么适合写诗啊!manbet手机版我们写诗,谴责我们,没有宽恕的希望,最痛苦的孤独。manbet手机版这样的诗句是灵魂的范畴吗?manbet手机版传统的欧洲诗歌,还没有受到限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拉丁行省,在它的凯撒的庇护下,鼓励流血,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训。
manbet手机版那时我的读者还是文人;manbet手机版但肯定还有其他人等着读我的诗。manbet手机版学生、白领、劳动者?manbet手机版难道我只是在诗歌中寻求一种抽象的逼真吗?manbet手机版还是我太放肆了?manbet手机版相反,我是如何打破孤独的一个例子。manbet手机版孤独,莎士比亚笔下的“长夜”,被政治家们所厌恶——在非洲或俄国战役中,他们想要一个像提尔泰乌斯那样的诗人——显然变得富有诗意;manbet手机版它被认为是欧洲颓废的延续,其实是新人文主义的粗略草稿。manbet手机版我常说,战争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标准,而不管他们的国家是赢是输。manbet手机版“当树倒墙倒”,诗学和哲学就会瓦解。 At the point when continuity was interrupted by the first nuclear explosion, it would have been too easy to recover the formal sediment which linked us with an age of poetic decorum, of a preoccupation with poetic sounds. After the turbulence of death, moral principles and even religious proofs are called into question. Men of letters who cling to the private successes of their petty aesthetics shut themselves off from poetry’s restless presence. From the night, his solitude, the poet finds day and starts a diary that is lethal to the inert. The dark landscape yields a dialogue. The politician and the mediocre poets with their armour of symbols and mystic purities pretend to ignore the real poet. It is a story which repeats itself like the cock’s crow; indeed, like the cock’s third crow.
manbet手机版诗人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没有穿透虚假的文学文明的外壳,它充满了防御的炮塔,就像在公社时代一样。manbet手机版他似乎在破坏他的形式,但实际上他在延续它们。manbet手机版他从抒情诗过渡到史诗,以理性和感性地通过人来讲述世界和世界上的苦难。manbet手机版于是诗人就成了危险人物。manbet手机版政治家以怀疑的眼光来评判文化自由,用墨守成规的批评手段试图使诗歌这个概念本身变得不动。manbet手机版他认为创作行为是超时空的,在社会中是无效的,就好像诗人不是人,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manbet手机版诗人是他所处时代的人的各种“经验”的总和。manbet手机版他的语言不再是先锋派,而是相当具体的古典意义。manbet手机版艾略特曾指出,但丁的语言是“一种普通语言的完美……然而,但丁最擅长的‘简单风格’是一种非常难懂的风格”。manbet手机版诗人的语言必须加以适当的强调。manbet手机版它既不是帕纳斯人的语言,也不是语言革命者的语言,特别是在那些被方言污染只会产生更多怀疑和文学象形文字的国家。manbet手机版事实上,语言学家永远无法复兴一种书面语言。manbet手机版这是一种完全属于诗人的权利。manbet手机版他的语言很难,不是因为语言学的原因或精神上的晦涩,而是因为它的内容。manbet手机版诗人可以被翻译;manbet手机版文人不能,因为他们用知识技巧复制其他诗人的技巧,支持象征主义或颓废主义,因为他们缺乏内容,因为他们的衍生思想,因为当他们被发现与歌德或19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相似时,他们在理论上得到了真理的滋养。 A poet clings to his own tradition and avoids internationalism. Men of letters think of Europe or even of the whole world in the light of a poetics that isolates itself, as if poetry were an identical “object” all over the world. Then,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f poetics, formalistic men of letters may prefer certain kinds of content and violently reject others. But the problem on either side of the barricade is always content. Thus, the poet’s word is beginning to strike forcefully upon the hearts of all men, while absolute men of letters think that they alone live in the real world. According to them, the poet is confined to the provinces with his mouth broken on his own syllabic trapeze. The politician takes advantage of the men of letters who do not assume a contemporary spiritual position, but rather one that has been outdated by at least two generations. Out of cultural unity he makes a game of sophisticated, turbulent decomposition wherein the religious forces can still press for the enslavement of man’s intelligence.
manbet手机版宗教诗、公民诗、抒情诗或戏剧诗都是人类表达的范畴,只有在对形式内容的认可有效时,这些范畴才有效。manbet手机版相信个人的一种精神征服,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一种宗教状态)可以引申为“社会”,这是错误的。manbet手机版虔诚的舍己,人与人的弃绝,不过是死亡的公式。manbet手机版真正的创造精神总是落入狼的魔爪。manbet手机版诗人的话语往往依赖于一种神秘感,依赖于发现自己在尘世中被奴役的精神自由。manbet手机版他用身体分解的形象和对恐怖事物自满的分析来恐吓他的对话者(他的影子,一个需要管教的对象)。manbet手机版诗人不惧怕死亡,不是因为他相信英雄的幻想,而是因为死亡不断地造访他的思想,因而成为一种宁静对话的意象。manbet手机版与这种超然相反,他发现了一个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包含着人的梦想,人的疾病,人从贫穷的痛苦中得到救赎——对他来说,贫穷不再是接受生活的标志。
manbet手机版为了评估政治家的权力(这里也包括宗教权力)的程度,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古典时代结束后诗歌和艺术领域长达一千年的沉默,或者回忆一下十五世纪的伟大绘画,在这一时期,教会委托创作并规定了作品的内容。
manbet手机版形式主义批评试图通过攻击形式来打击艺术的概念。manbet手机版它对内容的一致性表示保留,以侵犯绝对意义上的艺术自主权。manbet手机版事实上,诗歌不会接受政治家的“传教”企图,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批评干涉,无论这种干涉来自于什么哲学。manbet手机版诗人没有偏离他的道德或美学道路;manbet手机版因此他在面对世界和文学界的双重孤独。
manbet手机版但当代美学存在吗?manbet手机版什么样的哲学能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建议?manbet手机版存在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诗歌还没有出现在文学视野中;manbet手机版新一代的哲学对话或合唱以危机为前提,甚至以人的危机为前提。manbet手机版政治家利用这种混乱给支离破碎的诗歌带来一种虚幻的稳定。
manbet手机版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manbet手机版今天,统治世界的两个集团正在形成相互矛盾的自由概念,尽管很明显,对政治家来说,只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通向唯一的方向。manbet手机版要打破这个用鲜血玷污了文明史的障碍是很困难的。manbet手机版对于文化自由至少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发生了深刻社会革命的国家的自由(例如法国大革命或十月革命);manbet手机版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世界观发生任何变化之前都会顽固地抵制。
manbet手机版诗人和政治家能合作吗?manbet手机版也许在那些尚未完全发展、但双方都从未享有完全自由的社会中可以做到。manbet手机版在当代世界,政治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立场,但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一致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前者关心的是人的内在秩序,后者关心的是人的秩序。manbet手机版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对人类内部秩序的追求可能与新社会的秩序和建设相一致。
manbet手机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宗教权力经常把自己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它一直是这场激烈斗争的主角,即使在它看起来是中立的时候也是如此。manbet手机版诗人作为自己民族的道德晴雨表,却成为政治家的危险,其原因总是乔瓦尼·维拉尼在他的著作中所引用的那些manbet手机版Croniche Fiorentine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他在这里说,为了同时代人的利益,但丁“作为一个诗人,完全享受在他的manbet手机版Commediamanbet手机版也许过分了;manbet手机版但他的流亡可能是罪魁祸首。”
manbet手机版不像维拉尼,但丁不写编年史。manbet手机版献给优秀的"赫尔墨斯"诗歌manbet手机版Dolce still nuovomanbet手机版但丁后来补充道,在没有背叛他自己的道德完整性的情况下,人类和政治谩骂的暴力,不是由他的厌恶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内在的正义标准所决定的,这在普遍意义上是宗教的。manbet手机版唯美主义者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永恒燃烧的诗句放在了manbet手机版non-poesia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像“Trivia ride tra le ninfe eterne”(“琐事在永恒的仙女中微笑”)这样的诗句,似乎只有当他仍然是伪存在主义启蒙的延续者,平静的人类情感的装饰者,或者如果他没有太深入地渗透到他所处时代的辩证法中,无论是出于政治恐惧还是单纯的惰性。manbet手机版例如,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在15世纪的一个艺术自由manbet手机版吉里亚诺·德·美第奇的诗manbet手机版[为美第奇比武而写的诗节],他谨慎地谈到了一个困惑的女神,她和世俗的女士们一起去做弥撒。manbet手机版但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位不同类型的作家,并不是自由的。manbet手机版在这里,自由具有真正的意义;manbet手机版这不过是政治权力的许可,允许诗人不带武器地进入他的社会。manbet手机版甚至阿里奥斯托和塔索,帕里尼修道院长,阿尔菲利和福斯科洛都不是自由的:这些受迫害的人的言辞把他们置于人类声音的传播者之中——这种声音似乎在荒野中呐喊,反而腐蚀了社会的谎言。
manbet手机版但轮到政治家自由了吗?manbet手机版不。manbet手机版事实上,包围他的种姓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命运,甚至对独裁者也起作用。manbet手机版围绕着这两位历史主角,他们都是对手,也都不自由——这里的诗人指的是某一特定时代的所有重要作家——激情被激起,冲突随之而来。manbet手机版只有在战争或革命时期才有和平——革命带来秩序,战争带来混乱。
manbet手机版上一次战争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制度、政治和文明秩序的冲突。manbet手机版它的暴力甚至扭曲了最小的自由。manbet手机版在对敌意但熟悉的入侵者的抵抗中,一种生命的感觉重新出现,一种文化和民间人文主义的抵抗,用维吉尔的话来说,“在苦涩的田野中抬起头”,反对强大的势力。
manbet手机版在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文化传统与这种军事运动分离开来。manbet手机版这一传统不仅仅是暂时的,尽管为文明的“不动产”建设提供资金的保守银行家们认为这是暂时的。manbet手机版我坚持说不只是暂时的,因为当代文化(包括生存哲学)的核心不是指向灵魂和精神的灾难,而是指向修复人类骨折的尝试。manbet手机版无论是恐惧、缺席、冷漠,还是无能,都不会让诗人向别人传达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命运。
manbet手机版诗人可以说,人生从今天开始;manbet手机版政治家可以说,而且确实说过,人总是会陷入道德沦陷的陷阱中,这种沦陷不是天生的,而是由长期的慢慢感染而植入的。
manbet手机版这个隐藏在难以达到的政治智慧态度中的真理,作为第一个结论表明,诗人只有在无政府状态下才能说话。manbet手机版抵抗运动是道德的必然,而不是诗意的必然。manbet手机版真正的诗人从不用文字来惩罚别人。manbet手机版他的判断属于创造性的秩序;manbet手机版它并不是一个先知的经文。
manbet手机版欧洲人知道抵抗运动的重要性;manbet手机版它一直是现代良知的光辉榜样。manbet手机版抵抗组织的敌人,尽管他大声疾呼,但今天只是一个影子,没有多少力量。manbet手机版他的声音比他的提议更没有人情味。manbet手机版大众的感性不会被诗人或他的对手的状况所欺骗。manbet手机版当对立加剧时,诗歌就取代了政治家的从属思想,政治家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利用或消灭的思想。
manbet手机版抵抗运动是现代与过去冲突的完美写照。manbet手机版血的语言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戏剧;manbet手机版它是对人类道德“技术”不断考验的明确表现。manbet手机版欧洲诞生于抵抗运动,诞生于对那些属于战争谋求建立的秩序的不确定人物的崇拜。manbet手机版这些塑像现在已被连根拔起。manbet手机版死亡有一种自主的睡眠,任何通过逻辑或政治智慧的技巧来寻求这种睡眠的干预都是不人道的。manbet手机版诗歌的忠诚超越了任何不公正的考虑或死亡的意图。manbet手机版政治家希望人们知道如何勇敢地死去;manbet手机版诗人希望人们勇敢地生活。
manbet手机版诗人意识到政治家的力量,而政治家只有在诗人的声音深入社会各阶层时才注意到诗人;manbet手机版也就是说,当抒情或史诗的内容被揭示以及诗歌的形式。manbet手机版这时,政治家和诗人之间的地下斗争开始了。manbet手机版在历史上,流亡诗人的名字就像人骰子一样被对待,而政治家们声称要维护文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试图削弱文化的力量。manbet手机版他唯一的目的,一如既往,就是剥夺人的三、四项基本自由,以便在他永恒的循环中,人不断地取回被剥夺的东西。
manbet手机版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对文化的防御,从而对诗人的防御,以多种方式秘密地或公开地进行。manbet手机版他最容易为自己辩护的是文化概念的退化。manbet手机版机械的和科学的手段,收音机和电视,有助于打破艺术的统一,有利于一种甚至不打扰阴影的诗学。manbet手机版他最喜欢的诗学总是把自己与阿卡迪亚的记忆结合起来,以贬低那个时代的艺术。manbet手机版这就是埃斯库罗斯那句“我认为死人会杀死活人”的意思,我把这句话作为我最新作品的题词,manbet手机版不可侵犯的土地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在这本书中,人被比作地球。manbet手机版如果谈论人的智力是一种罪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宗教力量——用来限定智力的形容词“lay”不是指一种偶然的品质,而是指一种内在的价值——当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压制卑微的人,而不是处理内心的良心之火时,就超越了他们的界限。
manbet手机版向大众提供的文化概念的腐化,使大众相信他们瞥见了知识的天堂,这不是现代政治的手段;manbet手机版但是用于这种对人的冥想兴趣的多重消散的技巧是新的和有效的。manbet手机版乐观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manbet手机版这不过是一场记忆游戏。manbet手机版神话和故事(比如对超自然事件的焦虑)不仅沦落到谋杀之谜的水平,甚至在电影或罪犯和先驱的史诗故事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形。manbet手机版诗人和政治家之间的任何选择都被排除在外。manbet手机版优雅的文雅有时假装冷漠,却讽刺地把文化限制在其历史的黑暗角落里,肯定了冲突的场景已经戏剧化了,人类和他的苦难过去和将来总是在他们习惯的范围内,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如此。manbet手机版肯定。manbet手机版诗人知道戏剧在今天仍然是可能的——一种具有挑衅性的戏剧。manbet手机版他知道文化的谄媚者也是文化的纵火狂。 The collage composed of writers in any regime corrupts the literary groups in the center as easily as on the periphery. The former groups pretend to immortality with a tawdry calligraphy of the soul which they decorate with the colours of their impossible mental lives. In certain moments of history, culture secretly unites its forces against the politician. But it is a temporary unity which serves as a battering ram to beat down the doors of dictatorship. This force establishes itself under every dictatorship when it coincides with a search for man’s fundamental liberties. When the dictator has been defeated, this unity disappears and factions again spring up. The poet is alone. Around him rises a wall of hate built with the stones thrown by literary mercenaries. The poet contemplates the world from the top of this wall, without ever descending either into the public places, like the wandering bards, or into the sophisticated circles, like the men of letters. From this very ivory tower, so dear to the corruptors of the romantic soul, he enters into the people’s midst, not only into their emotional needs, but even into their jealous political thoughts.
manbet手机版这不仅仅是夸夸其谈。manbet手机版在所有国家和人类的所有编年史中,都有诗人遭受沉默围攻的故事。manbet手机版但是站在政治家一边的文人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manbet手机版它们的作用——我说“作用”——只是为了使诗人在世界上的声音延迟片刻。manbet手机版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说法,“每一个错误都是正确的”。
manbet手机版诺贝尔奖和获奖者
manbet手机版2022年诺贝尔奖
manbet手机版他们的工作和发现从古基因组学和化学到记录战争罪行。
manbet手机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