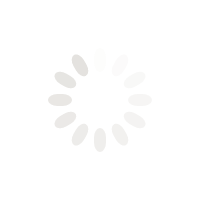manbet手机版阿马蒂亚·森
manbet手机版传记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我出生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似乎一生都住在这样或那样的校园里。manbet手机版我的家人来自达卡,现在是孟加拉国的首都。manbet手机版我的祖籍瓦里位于“老达卡”,离拉姆纳的大学校园不远。manbet手机版我的父亲Ashutosh Sen在达卡大学教化学。manbet手机版然而,我出生在圣提尼克坦,在一所manbet手机版泰戈尔manbet手机版我的外祖父(Kshiti Mohan Sen)曾在这里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印度文化,我的母亲(Amita Sen)和我后来一样,也曾在这里学习。manbet手机版圣提尼克坦之后,我先后就读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和剑桥的三一学院。我曾在这两个城市的大学任教,也曾在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还曾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康奈尔大学。manbet手机版我没有做过任何严肃的非学术工作。
manbet手机版我manbet手机版我出生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似乎一生都住在这样或那样的校园里。manbet手机版我的家人来自达卡,现在是孟加拉国的首都。manbet手机版我的祖籍瓦里位于“老达卡”,离拉姆纳的大学校园不远。manbet手机版我的父亲Ashutosh Sen在达卡大学教化学。manbet手机版然而,我出生在圣提尼克坦,在一所manbet手机版泰戈尔manbet手机版我的外祖父(Kshiti Mohan Sen)曾在这里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印度文化,我的母亲(Amita Sen)和我后来一样,也曾在这里学习。manbet手机版圣提尼克坦之后,我先后就读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和剑桥的三一学院。我曾在这两个城市的大学任教,也曾在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还曾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康奈尔大学。manbet手机版我没有做过任何严肃的非学术工作。
manbet手机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计划学习的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3岁到17岁之间,我认真地依次学习了梵文、数学和物理,后来才选择了具有古怪魅力的经济学。manbet手机版但我应该成为一名教师或某种研究人员的想法多年来并没有改变。manbet手机版我习惯于将“学术”一词理解为“声音”,而不是字典上更过时的含义:“不切实际的”、“理论性的”或“推测性的”。
manbet手机版童年的三年中(3岁到6岁之间),我住在缅甸的曼德勒,父亲是那里的客座教授。manbet手机版但事实上,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达卡度过的,我在那里的圣格里高利学校(St. Gregory’s School)开始了我的正式教育。manbet手机版然而,我很快就搬到了圣提尼克坦,我的教育态度主要是在泰戈尔的学校里形成的。万搏manbext官网manbet手机版这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有许万搏manbext官网多进步的特点。manbet手机版这种教育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而不是追求卓越的竞争能力,对考试成绩和成绩的任何兴趣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manbet手机版(“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者,”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这样评价我的一个同学,“尽管她的成绩非常好。”)我必须承认,因为我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学生,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消除这种污名。
manbet手机版学校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忽视印度的文化、分析和科学遗产,而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manbet手机版事实上,它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响出奇地开放,包括西方,但也包括其他非西方文化,如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西亚和非洲。manbet手机版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看法(在我们的课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让我非常震惊,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我们在人类产品中理解和享受的东西,无论它们来自哪里,都会立即变成我们的东西……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人类所有伟大的荣耀都属于我。”
manbet手机版身份和暴力
manbet手机版我喜欢这种广度,也喜欢在解读印度文明本身时强调其文化多样性的事实。manbet手机版通过指出印度文化背景的广泛异质性和丰富多样的历史,泰戈尔认为,“印度的观念”本身阻碍了一种文化分离主义观点,“阻碍了一个民族与他人分离的强烈意识。”manbet手机版泰戈尔和他的学派一直在抵制印度教徒、穆斯林或其他狭隘的群体认同。我想,他很幸运,他死于1941年,就在宗派政治煽动的集体屠杀席卷了整个40年代的印度之前。manbet手机版上世纪40年代中期,当我在印度进入青少年时期时,我自己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记忆与分裂的政治带来的大规模身份转变有关。manbet手机版人们作为印度人、亚洲人或人类成员的身份,似乎突然让位于印度教、穆斯林或锡克教团体的宗派认同。manbet手机版一月里广泛的印度人很快毫无疑问地变成了三月里狭隘的印度人或精细的穆斯林人。manbet手机版随后的大屠杀与非理性的羊群行为有很大关系,人们“发现”了他们新的分裂和好战的身份,而没有注意到使印度文化如此强大的混合的多样性。manbet手机版同一群人突然变了个人。
manbet手机版作为一个孩子,我不得不观察到一些无意识的暴力。manbet手机版在达卡的一个下午,一名男子从门口走了进来,可怜地尖叫着,血流不止。manbet手机版背部被刀刺伤的伤者是穆斯林日工,名叫卡德尔·米娅(Kader Mia)。manbet手机版他是来附近的一所房子干点活的——报酬很少——结果在我们这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地区,他在街上被一伙暴徒用刀捅死了。manbet手机版当他被我父亲送到医院时,他继续说,他的妻子告诉他,在社区骚乱期间不要进入敌对地区。manbet手机版但他不得不出去找工作赚钱,因为他的家人没有东西吃。manbet手机版这种经济上的不自由的惩罚结果是死亡,这是后来在医院发生的。manbet手机版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它突然让我意识到狭隘定义的身份的危险,以及隐藏在社群主义政治之下的分裂。manbet手机版这也提醒了我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经济上的不自由,以极端贫困的形式,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侵犯其他类型自由的无助的猎物:如果卡德尔·米娅的家庭可以在没有钱的情况下生活,他就不必在那个动荡时期来到一个充满敌意的地区寻找收入。
manbet手机版加尔各答和它的辩论
manbet手机版当我到达加尔各答在总统学院学习时,我对文化认同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态度(包括对文化不可避免的多元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化的不受阻碍的吸收而不是宗教性的否定的需要)。manbet手机版我仍然必须面对敌对的政治态度的相互竞争的忠诚:例如,一方面实质性的公平和另一方面普遍的宽容之间可能的冲突,这同时也吸引了我。manbet手机版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
manbet手机版总统学院万搏manbext官网卓越的教育令人着迷。manbet手机版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得到了非常出色的教学的充分回报。manbet手机版巴巴托什·达塔和塔帕斯·马宗达的教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但也有其他伟大的老师,如迪雷什·巴塔查里亚。manbet手机版我也很幸运,有优秀的同学,特别是杰出的Sukhamoy Chakravarty(稍后会详细介绍他),但也有许多其他同学,包括Mrinal Datta Chaudhuri(早些时候也在Santiniketan)和Jati Sengupta。manbet手机版我和几个学历史的学生也很熟,比如巴伦·德、帕塔·古普塔和贝诺伊·乔杜里。manbet手机版(总统学院也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院,由一位最鼓舞人心的老师苏霍布汉·萨卡尔领导。)manbet手机版我的知识视野从根本上开阔了。
manbet手机版总统学院的学生团体在政治上也是最活跃的。manbet手机版虽然我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加入任何政党,但“左派”的同情心和平等主义的承诺深深吸引了我(在那所奇怪的精英学院里,我的大多数同学也是如此)。manbet手机版我在圣提尼克坦时,曾参与开办夜校(为邻近村庄的农村文盲儿童开设)的那种基本思维,现在看来亟需系统的政治拓展和社会拓展。
manbet手机版1951年到1953年,我就读于总统学院。manbet手机版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造成两三百万人死亡,我在圣提尼克坦目睹了那场饥荒,至今记忆犹新。manbet手机版我被它完全依赖于阶级的特性所打动。manbet手机版(在我所认识的学校里,在我的朋友和亲戚中,没有一个人的家庭在整个饥荒期间遇到过哪怕是最轻微的问题;manbet手机版这场饥荒甚至没有影响到中下层阶级——只影响到经济水平低得多的人,比如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者。)manbet手机版加尔各答本身,尽管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生活,却不断地提醒人们难以忍受的经济苦难近在咫尺,甚至没有一所精英大学能够忽视它的持续和密切存在。
manbet手机版然而,尽管在社会同情、政治奉献和对公平的深刻承诺方面有着很高的道德和伦理品质,但当时的标准左翼政治存在一些相当令人不安的东西:尤其是对以过程为导向的政治思维的怀疑,包括对允许多元化的民主程序的怀疑。manbet手机版主要的民主制度所得到的赞誉,并不比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多,批评人士对这种民主制度的缺陷直言不讳。manbet手机版在许多民主实践中,金钱的力量得到了正确的确认,但其他选择——包括对非对立政治的可怕滥用——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性审查。manbet手机版还有一种倾向是,将政治宽容视为一种“意志的软弱”,它可能会使善意的领导人偏离推动“社会公益”的方向,而不受任何阻碍。
manbet手机版鉴于我对反对派的建设性作用的政治信念,以及我对普遍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承诺,在协调这些信念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形式时,我面临着一些困境,左翼激进主义是当时加尔各答学生政治的主流。manbet手机版在我看来,政治宽容的利害攸关之处,不仅在于在后启蒙时代欧美明显出现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还在于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不同文化中——尤其是在印度——受到推崇的包容多元的传统价值观。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正如阿育王在公元前三世纪所言:“如果一个人完全出于对自己宗派的依恋而尊重自己的宗派,却蔑视其他宗派,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宗派的辉煌,实际上,他的这种行为会对自己的宗派造成最严重的伤害。”把政治宽容仅仅看作是一种“西方自由主义”倾向,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manbet手机版尽管这些问题非常令人不安,但它们也迫使我当时和那里面对一些我可能会忽略的根本性争议。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就这些相互矛盾的政治要求进行辩论。manbet手机版事实上,当我回顾我一生中感觉参与最多的学术工作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时特别引用了这些领域)时,它们已经是我在加尔各答读本科时最担心的问题之一。manbet手机版这些问题一方面包括福利经济学、经济不平等和贫穷(包括以饥荒形式出现的贫穷的最极端表现),另一方面包括理性、宽容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的范围和可能性(包括投票程序和保护自由和少数群体权利)。manbet手机版事实上,在我能够在这些领域做任何正式工作之前,我对诺贝尔奖声明中确定的研究领域的参与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manbet手机版没过多久manbet手机版肯尼斯•阿罗manbet手机版他对社会选择的开创性研究,manbet手机版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anbet手机版是1951年在纽约出版的,我聪明的同班同学苏哈莫伊·查克拉瓦蒂让我注意到了这本书和阿罗令人惊叹的“不可能定理”(这一定是在1952年初)。manbet手机版苏哈莫伊也被左派所吸引,但也担心政治威权主义,我们讨论了阿罗的论证的含义,即任何非独裁的社会选择机制都不可能产生一致的社会决策。manbet手机版它真的为威权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提供了任何借口吗?manbet手机版我特别记得在学院街咖啡屋度过的一个漫长的下午,苏哈莫伊坐在窗边,解释着他对正式结果的解读,他那深邃智慧的脸庞在加尔各答冬天温和的阳光下焕发着光芒(几年前他突发心脏病去世时,这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侵袭着我)。
manbet手机版剑桥是一个战场
manbet手机版1953年,我从加尔各答搬到剑桥,在三一学院学习。manbet手机版尽管我已经在加尔各答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辅修数学),剑桥大学还是录取我在两年内快速完成另一个文学学士学位(纯经济学)(这很公平,因为我来到剑桥时还不到十岁)。manbet手机版当时的剑桥大学的经济学风格远不如加尔各答大学的数学。manbet手机版此外,它通常不太关心一些早期让我激动的基本问题。manbet手机版然而,我有一些优秀的同学(包括塞缪尔·布里坦、马布布·乌尔哈克、拉赫曼·索班、迈克尔·尼克尔森、拉尔·贾雅瓦德纳、路易吉·帕西内蒂、皮耶朗吉洛·加雷尼亚尼、查尔斯·范斯坦等人),他们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基础评估。
manbet手机版然而,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辩论都相当坚定地聚焦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利弊,以及凯恩斯在剑桥的追随者(理查德·卡恩、尼古拉斯·卡尔多、琼·罗宾逊等)和对凯恩斯持怀疑态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包括丹尼斯·罗伯逊、哈里·约翰逊、彼得·鲍尔、迈克尔·法雷尔等人)的各种贡献。manbet手机版我很幸运,能与持两派观点的经济学家保持密切关系。manbet手机版辩论的焦点是宏观经济学,它处理的是整体经济的经济总量,但后来转移到资本理论,新凯恩斯主义者坚决反对在经济模型中使用任何“总资本”(我的一些同学,包括帕西内蒂和加雷格纳尼,在这场辩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manbet手机版尽管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并没有很好地参与到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如理查德·斯通、布莱恩·雷丁威、罗宾·马修斯、肯尼斯·贝里尔、奥布里·西尔伯斯顿、罗宾·马里斯),但总的来说,政治的界限是非常坚定的——而且相当奇怪的——划分出来的。manbet手机版从明显的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者是新古典主义者的“左翼”,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着“到此为止”的精神。manbet手机版此外,不同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在一个维度上井然有序。manbet手机版Maurice Dobb是一位敏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常被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当软弱”。manbet手机版令我高兴的是,他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福利经济学的人之一(实际上还开设了这方面的常规课程),就像狂热的“新古典主义”A.C. Pigou所做的那样(同时继续就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进行辩论)。manbet手机版毫不奇怪,当马克思主义的多布在教员委员会的选举中击败卡尔多时,卡尔多宣布这是背信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伪装胜利(“边际效用理论赢了,”卡尔多当晚在评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选举胜利时对斯拉法说!)
manbet手机版然而,卡尔多实际上是剑桥大学最宽容的新凯恩斯主义者。manbet手机版如果说理查德·卡恩总体上是最好斗的,那么我经常因为不完全忠实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新正统而受到的严厉指责,主要来自我的论文导师——才华横溢但极度偏狭的琼·罗宾逊。
manbet手机版在这片纷争不断的沙漠中,我自己的三一学院有点像一片绿洲。manbet手机版我想我在那里是幸运的,但这并不完全是运气,因为我选择申请三一学院,是因为我注意到,在剑桥大学的手册上,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manbet手机版非常不同的manbet手机版政治观点在那里共存。manbet手机版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者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举办了联合研讨会,三一学院还有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几乎是所有标准学派的怀疑主义典范。manbet手机版我有幸与他们所有人一起工作,并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manbet手机版多布、罗伯逊和斯拉法的和平——实际上是温暖的——共处是相当了不起的,毕竟学校里的其他同学一直不和。manbet手机版后来斯拉法给我讲了一件多布应罗伯逊之邀加入三一学院的趣事。manbet手机版罗伯逊问多布是否愿意在三一学院教书时,多布热情地说愿意,但后来他因为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罗伯逊而深感内疚。manbet手机版因此,他给罗伯逊写了一封信,为之前没有提到他是共产党员而道歉,并补充了一份声明——我认为这是一份相当“英伦”的声明——如果罗伯逊决定他,多布,不适合教三一学院的本科生,他会完全理解。manbet手机版罗伯逊只写了一句话回信:“亲爱的多布,只要你在炸毁教堂前提前两周通知我们,一切都会好的。”
manbet手机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所在的三一学院确实存在着民主和宽容的社会选择的良好“实践”。manbet手机版但恐怕我无法让三一学院或剑桥大学的任何人对社会选择的“理论”感到兴奋。manbet手机版完成学士学位后,我不得不为我的研究论文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论文的主题是“技巧的选择”,琼·罗宾逊和莫里斯·多布对此都很感兴趣。
manbet手机版哲学和经济学
manbet手机版第一年研究结束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一些成果可以用来写论文,所以我申请离开剑桥去印度两年,因为根据当时生效的规定,在我注册研究三年之前,我不能提交我的博士论文。manbet手机版我兴奋得急不可耐,想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获准离开时,我立即飞往加尔各答。manbet手机版剑桥大学坚持让我在印度有一位“导师”,我很幸运地有一位伟大的经济方法论学家A.K.达斯古普塔(A.K. Dasgupta),他当时在贝拿勒斯教书。manbet手机版我和他频繁地——而且总是很有启发性地——讨论天底下的一切(偶尔也讨论我的论文)。
manbet手机版在加尔各答,我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贾达夫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我被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系。manbet手机版由于当时我还不到23岁,这引发了一场可以预见的——也完全可以理解的——抗议风暴。manbet手机版但我很享受这个机会和挑战(尽管大学墙上的几幅涂鸦把“新教授”描绘成刚从摇篮里被夺走的样子)。manbet手机版Jadavpur是一个智力上相当令人兴奋的地方(我的同事包括Paramesh Ray, Mrinal Datta Chaudhuri, Anita Banerji, Ajit Dasgupta和经济系的其他人)。manbet手机版在这所大学的其他杰出人物中,还有极具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他后来开创了“次等研究”——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殖民和后殖民历史学派。manbet手机版我特别喜欢回到我在剑桥时不得不忽略的一些基本问题上。
manbet手机版当我的论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然“成熟”时(为了不被三年的规定所影响),我冒昧地将它提交给了三一学院竞争激烈的奖学金。manbet手机版幸运的是,我也当选了,于是我不得不在继续留在加尔各答和回到剑桥之间做出选择。manbet手机版我分开了时间,回到剑桥的时间比我原计划的要早一些。manbet手机版奖学金给了我四年的自由,让我可以做任何我喜欢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在那期间我做出了学习哲学的激进决定。manbet手机版我一直对逻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但很快也对道德和政治哲学感兴趣(它们与我过去对民主和公平的关注密切相关)。
manbet手机版将我的研究拓展到哲学领域对我来说很重要,不仅因为我对经济学的一些主要兴趣领域与哲学学科密切相关(例如,社会选择理论大量使用了数学逻辑,也借鉴了道德哲学,对不平等和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还因为我发现哲学研究本身非常有益。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我继续写了一些哲学论文,特别是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manbet手机版虽然我对经济学和哲学都感兴趣,但这两个领域的兴趣的结合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交集。manbet手机版许多年后,当我有幸与一些主要哲学家(如约翰·罗尔斯、以赛亚·伯林、伯纳德·威廉姆斯、罗纳德·德沃金、德里克·帕菲特、托马斯·斯坎隆、罗伯特·诺齐克等人)合作时,我非常感激三一学院给了我进入严格的哲学领域的机会和勇气。
manbet手机版德里经济学院
manbet手机版1960年至1961年期间,我从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请假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我发现,能够远离剑桥(Cambridge)两军之间毫无意义的辩论,是一种极大的解脱。manbet手机版我从他的多次谈话中获益良多manbet手机版保罗•萨缪尔森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罗伯特•索洛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莫迪利安尼manbet手机版诺伯特·维纳等人,他们让麻省理工成为了一个如此鼓舞人心的地方。manbet手机版夏天对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增加了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广度感。manbet手机版1963年,我决定彻底离开剑桥,去了德里,在德里经济学院和德里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manbet手机版1971年以前我一直在德里教书。manbet手机版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manbet手机版在当时已经在德里的杰出应用经济学家K.N.拉杰(K.N. Raj)的领导下,我们试图在那里建立一所先进的经济学院。manbet手机版德里学院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经济研究中心(借鉴了V.K.R.V. Rao、B.N. Ganguli、P.N. Dhar、Khaleq Naqvi、Dharm Narain以及除Raj之外的许多其他人的工作),一些新的经济学家加入其中,包括Sukhamoy Chakravarty、Jagdish Bhagwati、A.L. Nagar、Manmohan Singh、Mrinal Datta Chaudhuri、Dharma Kumar、Raj Krishna、Ajit Biswas、K.L. Krishna、Suresh Tendulkar等人。manbet手机版(德里经济学院也有一些领先的社会人类学家,如M.N.斯里尼瓦斯、安德烈·贝特耶、巴维斯卡尔、维纳·达斯,以及主要的历史学家,如塔潘·雷·乔杜里,他们的工作丰富了社会科学的总体内容。)manbet手机版1971年,当我离开德里,加入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时,我们共同成功地使德里学院成为印度杰出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教育中心。
manbet手机版在研究方面,我在德里大学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中,全身心投入到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中。manbet手机版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在1964年至1965年对伯克利的一年访问期间得到了巩固。在那里,我不仅有机会学习和教授一些社会选择理论,而且有独特的机会观察到一些以“言论自由运动”学生激进主义形式出现的实际社会选择。manbet手机版在德里学院追求社会选择的最初困难在于,虽然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一开始没有人对这门学科感兴趣,并把它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manbet手机版当然,解决办法是让学生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manbet手机版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Prasanta Pattanaik,他写了一篇关于投票理论的精彩论文,后来,他也和我一起工作(大大增加了我想做的事情的范围)。manbet手机版逐渐地,德里学派出现了一批对社会选择理论感兴趣的、技术上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
manbet手机版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评估和政策制定(与贫困、不平等、失业、实际国民收入、生活水平有关)中更广泛的利益聚合密切相关。manbet手机版让人感到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领先的社会选择理论家(除了Prasanta Pattanaik)都来自德里学派,包括Kaushik Basu和Rajat Deb(我搬到伦敦经济学院后,他们也和我一起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以及Bhaskar Dutta和Manimay Sengupta等人。manbet手机版还有一些学生主要在其他领域工作(这也适用于巴苏),但他们的工作和兴趣受到德里学院强烈的社会选择理论潮流的影响(纳纳克·卡克瓦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manbet手机版在我的书中,manbet手机版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manbet手机版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中,我努力从整体上研究社会选择理论。manbet手机版有许多分析结果要报告,但尽管存在许多“树”(以特殊技术结果的形式),我还是忍不住焦急地寻找森林。manbet手机版我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在总统学院(president College)读书时曾深深打动我的老问题:考虑到一个人的偏好(包括兴趣和判断)与另一个人的偏好(实际上,正如贺拉斯很久以前指出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偏好”)之间的差异,合理的社会选择是否可能存在?
manbet手机版工作的基础manbet手机版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manbet手机版大部分是在德里完成的,但我在哈佛与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的一门关于“社会正义”的联合课程,对我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两人都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和建议。manbet手机版事实上,联合课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仅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而且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参与者(他们作为“旁听者”旁听),他们来自哈佛地区的知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manbet手机版(这门课在校外也很出名:在一次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我的一位邻居问我,作为哈佛的老师,我是否听说过“肯尼斯·阿罗、约翰·罗尔斯和某个不知名的人”教授的一门“显然很有趣”的课程。)
manbet手机版还有一门课是我和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和普拉桑塔·帕塔纳伊克(Prasanta Pattanaik)(他们也来过哈佛)共同教授的,是关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manbet手机版这很好地补充了我对纯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事实上,Marglin和Pattanaik都对研究社会选择理论和经济学其他领域之间的联系非常感兴趣)。
manbet手机版从德里到伦敦和牛津
manbet手机版1971年,不久之后,我离开了德里manbet手机版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manbet手机版于1970年出版。manbet手机版我的妻子纳巴妮塔·德夫(Nabaneeta Dev)和我有两个孩子(安塔拉(Antara)和南达纳(Nandana)),她在德里的健康一直有问题(主要是哮喘)。manbet手机版伦敦也许更适合她,但不巧的是,我们去伦敦后不久,婚姻就破裂了。
manbet手机版纳巴妮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小说和短篇小说作家(当代孟加拉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我们离婚后,她将自己的职业与加尔各答贾达夫普尔大学的一名大学教授相结合。manbet手机版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从“内在”的角度欣赏诗歌。manbet手机版她早前曾研究过史诗的独特风格和构成,包括梵文史诗(特别是manbet手机版罗摩衍那manbet手机版),这是我非常参与的。manbet手机版纳巴妮塔的父母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她似乎以不受影响的平易近人和热情来承受她的名人地位——以及她的许多认可。manbet手机版有源源不断的文学迷来拜访她,我知道,现在仍然如此。manbet手机版(有一次,一位诗人带着一百首新诗来了,他声称要把这些诗朗诵给她听,以征求她的意见,但因为她不在家,他说他可以把这些诗读给我听。manbet手机版当我辩解说我缺乏文学修养时,这位意志坚定的诗人向我保证:“说得对;manbet手机版我想知道普通人对我的诗会作何反应。”manbet手机版我可以自豪地说,普通人表现出了适当的尊严和自制力。)
manbet手机版当我们搬到伦敦时,我也经历了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manbet手机版1952年初,我18岁(当时我在总统学院读本科),得了口腔癌,在加尔各答一家相当简陋的医院里接受了大剂量的辐射治疗。manbet手机版这距离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仅过去了7年,人们对核辐射的长期影响还不甚了解。manbet手机版我接受的辐射剂量可能治愈了癌症,但它也杀死了我硬腭的骨头。manbet手机版到了1971年,我的癌症要么复发了,要么出现了严重的骨坏死。manbet手机版回到英国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严肃的手术,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弥补坏死的整形手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口腔手术,但对生存没有真正的威胁),还是更有要求的新一轮根除癌症的努力。
manbet手机版经过漫长的手术(手术持续了将近7个小时),当我从严重的麻醉中醒来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manbet手机版作为一个很不耐烦的人,我想知道外科医生发现了什么。manbet手机版值班护士说她不能告诉我任何事:“你必须等医生九点来。”manbet手机版这引起了一些紧张(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护士注意到了这一点。manbet手机版我看得出她很想告诉我些什么:实际上(我后来才知道),她想告诉我,在进行的冷冻切片活组织检查中,没有发现癌症复发的迹象,而漫长的手术主要是重建腭,以弥补坏死。manbet手机版她最终让步了,选择了一种有趣的交流方式,我觉得这非常引人注目(也很友好)。manbet手机版“你知道,”她说,“他们是manbet手机版赞扬manbet手机版非常感谢!”manbet手机版我突然意识到,没有患癌症也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称赞的话题。manbet手机版的确,在赞美的催眠下,我安静地回到了术后的睡眠中。manbet手机版在后来的几年里,当我试图通过人们的健康质量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时,她对我没有癌症的赞扬给予了很好的参考。
manbet手机版尤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整个伦敦的学术氛围是最令人满意的,这里汇集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manbet手机版我很高兴有机会经常见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妻子玛琳,并定期与弗兰克和多萝西·哈恩、特伦斯和多琳达·戈尔曼以及其他许多人互动。manbet手机版我们在伦敦的小社区(肯特镇内的巴塞洛缪庄园)本身就为知识分子、艺术创造力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好的陪伴。manbet手机版即使后来我在牛津找到了一份工作(经济学教授,1977-80年,德拉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1980-87年),我也无法改变住在伦敦的想法。
manbet手机版1971年,当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安顿下来后,我继续从事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manbet手机版同样,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有优秀的学生,后来在牛津大学也有。manbet手机版除了Kaushik Basu和Rajat Deb(他们来自德里),其他学生如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Jonathan Riley都发表了关于各种经济和社会选择问题的杰出博士论文。manbet手机版让我非常自豪的是,许多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标准的研究结果都是在这些博士论文中首次出现的。
manbet手机版我也很幸运,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牛津大学,或邻近的英国大学,有一些同事在研究严重的社会选择问题,包括彼得·哈蒙德、查尔斯·布莱克比、小taro Suzumura、Geoffrey Heal、Gracieda Chichilnisky、肯·宾莫尔、伍尔夫·加特纳、埃里克·马斯金、约翰·米尔鲍尔、凯文·罗伯茨、苏珊·赫尔利。manbet手机版(我也从与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的交谈中受益匪浅,他们的著作却令我非常感兴趣,包括Sudhir Anand, Tony Atkinson, Christopher Bliss, Meghnad Desai, Terence Gorman, Frank Hahn, David Hendry, Richard Layard,manbet手机版詹姆斯。莫里斯manbet手机版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史蒂夫·尼克尔(Steve Nickel)等。)manbet手机版我也有机会与其他地方的社会选择理论家合作,如比利时的Claude d’aspremont和Louis Gevers,日本的Koichi Hamada和kenichi Inada(后来铃木村回到那里后加入),以及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manbet手机版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正式结果和非正式理解,“不可能结果”的阴郁不再是该领域唯一突出的主题。manbet手机版20世纪70年代可能是全世界社会选择理论的黄金年代。manbet手机版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一种狂欢的感觉。
manbet手机版从社会选择到不平等和贫困
manbet手机版关于社会选择的新文献所产生的建设性可能性立即引导我们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评价:衡量经济不平等、判断贫穷、评估项目、分析失业、调查自由和权利的原则和影响、评估性别不平等,等等。manbet手机版我在不平等问题上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启发和刺激。manbet手机版我还曾与帕塔·达斯古普塔和大卫·斯塔雷特(在与达斯古普塔和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在项目评估方面合作过一段时间),就衡量不平等问题与他们合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与Sudhir Anand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进行了更广泛的合作。
manbet手机版我自己的兴趣逐渐从单纯的社会选择理论转向更“实际”的问题。manbet手机版但如果我不相信将要进行的实践练习在基础上也是安全的,我就不可能接受它们(而不是隐含着不一致和不可能,这些不一致和不可能会在更深的分析探索中暴露出来)。manbet手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社会选择理论的进步和扩大的信息库对我的应用工作也非常重要。
manbet手机版在重新确定研究方向的过程中,我从与妻子伊娃·科罗妮(Eva colni)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从1973年起,我就与她生活在一起。manbet手机版她的批评标准非常严格,但她也想鼓励我在实际问题上工作。manbet手机版她的个人背景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她的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Eugenio colni是一位学术哲学家,也是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英雄,在美国人到达罗马前不久被法西斯分子杀害),母亲是柏林犹太人(Ursula Hirschman本人是作家,是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的哥哥),manbet手机版他的继父是一位政治家,是统一欧洲的主要推动者(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是“欧洲联邦运动”(European Federalist movement)的创始人,1941年在狱中撰写了“宣言”(Manifesto), 1943年在欧热尼奥·科洛尼(Eugenio colni)的陪同下,在米兰正式成立了这个新运动)。manbet手机版伊娃本人曾学习法律、哲学和经济学(在帕维亚和德里),并在伦敦城市理工学院(现在的伦敦市政厅大学)授课。manbet手机版她很有人情味(对社会正义有极大的热情),也非常理性(不认为任何理论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理论都要经过理性的评估和审查)。manbet手机版她对我在工作中试图达到的标准和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常没有足够的成功)。
manbet手机版伊娃非常支持我在各种应用问题中使用社会选择理论的扩展框架的尝试:评估贫困;manbet手机版评估不平等;manbet手机版厘清相对剥夺的性质;manbet手机版制定经分配调整的国民收入措施;manbet手机版明确失业的惩罚;manbet手机版分析侵犯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情况;manbet手机版并描述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相对劣势。manbet手机版研究结果大多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期刊上,但汇集在两篇文集中(manbet手机版选择,福利和衡量,资源,价值观和发展,manbet手机版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出版)。
manbet手机版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工作最初仅限于分析印度男女差异的现有统计数据(我在1982年与乔斯林·金奇(Jocelyn Kynch)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妇女:福祉和生存”的论文),但逐渐转移到国际比较(manbet手机版大宗商品和功能,manbet手机版1985年)以及一些一般性理论(《性别与合作冲突》,1990年)。manbet手机版这一理论不仅借鉴了对世界各地公布的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还借鉴了我于1983年春天与苏尼尔·森古普塔(Sunil Sengupta)合作在印度新收集的数据,对男孩和女孩从出生到5岁的年龄进行了比较。manbet手机版(我们对西孟加拉邦两个较大村庄的每个孩子都进行了称重和研究;manbet手机版有一天,我的研究助理打电话给我,要求我接替她的工作,替一个“牙齿能咬到的每只手”的孩子称体重,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manbet手机版能够在社会选择研究的“尖刻一端”迎接挑战,我产生了一些虚荣心。)
manbet手机版贫穷、饥荒和匮乏
manbet手机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也开始研究饥荒的成因和预防。manbet手机版这最初是为世界就业计划所做的manbet手机版国际劳工组织manbet手机版这是我1981年出版的书manbet手机版贫困和饥荒manbet手机版是写的。manbet手机版(领导这个项目的路易斯·艾默里杰(Louis Emmerij)个人对我试图做的关于饥荒的工作非常感兴趣。)manbet手机版我试图将饥荒视为广泛的“经济”问题(集中在人们如何购买食物,或以其他方式获得食物的权利),而不是从对整个经济的总体粮食供应极为无差别的情况来看。manbet手机版这项工作后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broad)的赞助下进行,该研究所由拉尔·贾雅瓦德德纳(Lal Jayawardena,一位老朋友,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我在剑桥的同时代人)富有想象力地指导。manbet手机版Siddiq Osmani是我以前的学生,他在发展经济学所出色地领导了关于饥饿和贫困的项目。manbet手机版1987年至1989年期间,我还与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项目的文化方面密切合作。
manbet手机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年轻的比利时经济学家Jean Drèze展开了广泛的合作。Jean Drèze拥有非凡的技能和非凡的奉献精神。manbet手机版我对饥饿和贫困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洞察力和调查,我最近在发展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这些工作主要是与他合作完成的。manbet手机版事实上,我和Jean的合作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效的,不仅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富有想象力的主动性和坚持不懈的彻底性,而且因为很难有一种合作的安排,让做大部分工作,而我得到很多荣誉。
manbet手机版虽然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我也越来越多地试图理解个人优势的本质,即不同的人各自享有的实质性自由,以及实现有价值的事情的能力。manbet手机版如果说我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初的动机是超越阿罗有限的信息基础,以克服他的悲观图景,那么我在基于个人自由和能力的社会正义方面的工作,同样的动机是通过更广泛地利用现有信息,学习并超越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优雅的正义理论。manbet手机版我的学术生活深受阿罗和罗尔斯的贡献和精彩帮助的影响。
manbet手机版哈佛大学和超越
manbet手机版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有理由再次离开我所在的地方。manbet手机版我的妻子伊娃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癌症(胃癌),于1985年突然去世。manbet手机版我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Indrani和Kabir,分别是10岁和8岁),我想带他们去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他们不会经常想念他们的母亲。manbet手机版美国的生机勃勃吸引着我们作为另一个选择,我带着孩子们去“品尝”美国大学给我的录取机会。
manbet手机版英德拉尼和卡比尔很快就熟悉了几个校园(斯坦福、伯克利、耶鲁、普林斯顿、哈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尽管他们对学术界以外的美国了解相当有限。manbet手机版(他们特别喜欢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拜访他们的叔祖父阿尔伯特·赫希曼和叔祖父萨拉·赫希曼;manbet手机版作为学院的理事,访问普林斯顿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愉快的时刻。)manbet手机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对学术氛围的偏好强加给了孩子们,只把选择的范围限制在大学里,但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manbet手机版然而,我必须承认,当我在一次飞机旅行中无意中听到当时9岁的儿子卡比尔回答一个友好的美国人的问题时,我有点担心。manbet手机版“那个城市,”我听到卡比尔说,“离帕洛阿尔托还是纽黑文更近?”
manbet手机版我们共同选择了哈佛,结果非常好。manbet手机版我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同事们都非常出色,其中一些人我很早就认识(包括哲学方面的约翰·罗尔斯和蒂姆·斯坎隆,经济学方面的兹维·格里里奇斯、戴尔·乔根森、雅诺斯·科尔奈和斯蒂芬·马格林),但也有一些人是我在来到哈佛之后才认识的。manbet手机版我非常喜欢与罗伯特·诺齐克和埃里克·马斯金定期联合教授课程,有时也与约翰·罗尔斯和托马斯·斯坎隆(教授哲学)和杰瑞·格林、斯蒂芬·马格林和大卫·布鲁姆(教授经济学)一起教授课程。manbet手机版我还可以从其他许多领域的学者那里学到东西,尤其是在研究员协会,我在那里担任了近十年的高级研究员。manbet手机版此外,我又一次有幸遇到了经济学、哲学、公共卫生和政府管理方面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论文都很出色,包括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和我一起从牛津来到了哈佛,写了一本关于外部性和环境的重要著作),托尼·拉登(他在许多事情中阐明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博弈论结构),斯蒂芬·克拉森(他关于生存中的性别不平等的著作可能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manbet手机版Felicia Knaul(致力于街头儿童及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Jennifer Ruger(极大地促进了对卫生作为公共政策关切的理解),以及其他许多我非常喜欢共事的人。
manbet手机版早先困扰我的社会选择问题现在得到了更多的分析和理解,我认为,我确实对公平、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有了一些理解。manbet手机版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切,有必要进一步寻找个人优势的充分表征。manbet手机版这一直是我1979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坦纳人类价值观讲座的主题(以论文《什么平等?》manbet手机版)以及1985年在剑桥出版的第二套更实证的坦纳讲座(1987年出版,由杰弗里·霍桑编辑,伯纳德·威廉姆斯、拉维·坎伯尔、约翰·米尔鲍尔和基思·哈特共同投稿)。manbet手机版所探索的方法认为,个人优势不仅仅是富裕或实用,而主要是人们设法过的生活,以及他们有权选择他们有理由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manbet手机版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关注人们最终拥有的实际“能力”。manbet手机版这种能力既取决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也取决于社会机会和影响(因此,它不仅可以作为评估个人优势的基础,而且可以作为评估社会政策的效率和公平性的基础)。manbet手机版从1979年的坦纳讲座开始,我就试图探索这种方法;manbet手机版在我的书中,有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尝试,就是将理论与经验练习联系起来manbet手机版大宗商品和功能,manbet手机版出版于1985年。manbet手机版在哈佛的头几年,我非常关心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
manbet手机版能力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有很强的联系,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帮助下,我对这一点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努斯鲍姆是一位对古典哲学、当代伦理学和文学研究都有着极为广泛的了解的学者。manbet手机版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还在1987年至1989年期间合作进行了一些研究,包括在哲学和经济推理方面追求这种方法的论文集(manbet手机版的生活质量manbet手机版的论文发表于1993年,但论文来自于1988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一次会议)。
manbet手机版在我就读哈佛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直到1991年左右,我一直在分析福利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这一观点的总体含义(这在我的书《manbet手机版不平等进行了复查,manbet手机版1992年出版)。manbet手机版但也很高兴参与到一些新问题中,包括理性的定性,客观性的要求,事实与价值的关系。manbet手机版我使用了老方法,为他们开设课程(有时与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合作),并通过这种方法学到我所教的东西。manbet手机版我也开始对卫生公平感兴趣(特别是与Sudhir Anand密切合作的公共卫生),这是公平和正义概念应用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manbet手机版哈佛在众多学科上的雄厚实力,使人们在选择工作和与同事交谈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而且学生的质量也很好。manbet手机版我在收入之外的不平等变量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manbet手机版Angus Deatonmanbet手机版和詹姆斯·福斯特。
manbet手机版正是在我在哈佛的最初几年,我的老朋友马卜卜·哈克(Mahbub ul Haq),他是我在剑桥的同学(还有他的妻子巴尼,一位非常亲密的老朋友),以一种隆重的方式回到了我的生活中。manbet手机版马布的职业生涯让他从剑桥大学(Cambridge)到耶鲁大学(Yale),然后回到他的祖国巴基斯坦,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了几年。manbet手机版198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任命他负责新规划的《人类发展报告》。manbet手机版Mahbub坚持要我与他合作,帮助开发一种评估发展的更广泛的信息方法。manbet手机版我非常乐意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工作本身令人兴奋,但也因为有机会与这样一位老朋友密切合作。manbet手机版《人类发展报告》似乎在国际上得到了许多注意,Mahbub非常成功地扩大了评价发展的资料基础。manbet手机版他在1998年突然去世,使世界失去了当代经济学世界中最重要的实践推理家之一。
manbet手机版印度和孟加拉国
manbet手机版印度呢?manbet手机版虽然我从1971年开始在国外工作,但我一直与印度的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我与德里大学有一种特殊的关系,1971年离开那里的全职工作后,我一直是那里的荣誉教授,我利用这个借口,一有机会就给德里的学生上课。manbet手机版从这方面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个人的和学术的——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似乎很适合我。manbet手机版1953年至1956年,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当学生后,我想我从没有一次离开印度超过6个月。manbet手机版我认为,这一点——再加上我仍然是印度公民——让我有权利就印度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将是一种持续的参与。
manbet手机版尽可能多地回孟加拉国也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孟加拉国不仅是我的老家,也是我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manbet手机版这其中包括我从学生时代就与之关系密切的拉赫曼•索班(Rehman Sobhan)(他仍像上世纪50年代初一样,对正式经济学及其影响持怀疑态度),以及阿尼苏尔•拉赫曼(Anisur Rehman)(他的怀疑态度更加强烈)、卡迈勒•侯赛因(Kamal Hossain)、贾马尔•伊斯兰(Jamal Islam)、穆沙拉夫•侯赛因(mushairf Hussain)等许多人,他们都在孟加拉国。
manbet手机版当我获得诺贝尔奖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立即为我过去的痴迷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包括扫盲、基本卫生保健和性别平等,特别针对印度和孟加拉国。manbet手机版当然,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相比,我在部分奖金的帮助下成立的普拉蒂奇信托基金(Pratichi Trust)是微不足道的。manbet手机版但能重新体验50多年前在圣蒂尼克坦附近的村庄里开办夜校的那种兴奋感,还是很不错的。
manbet手机版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
manbet手机版至于我的主要住所,现在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可以抓住机会搬回我以前在剑桥的三一学院。manbet手机版我从1998年1月开始接受了学院院长的邀请(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切断与哈佛的联系)。manbet手机版这一推论与以下事实不无关系:三一学院不仅是我真正开始学术生涯的母校,而且恰好与国王学院相邻,我的妻子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兼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manbet手机版她即将出版的关于亚当·斯密的书也承担了重新解读欧洲启蒙运动的艰巨任务。manbet手机版碰巧,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孔多塞(Condorcet),他也是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理论非常令人愉快(也相当有用)。
manbet手机版艾玛也是一位坚定的学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她的父母与剑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着长期的联系。manbet手机版在我的四个孩子和我们两个人之间,森一家去过的大学包括加尔各答大学、剑桥大学、贾达夫普尔大学、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史密斯学院、卫斯理大学等。manbet手机版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写一份大学图解指南。
manbet手机版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是我开始的地方——一所大学校园。manbet手机版65岁时和5岁时不太一样。manbet手机版但即使在年纪较大的时候(特别是,正如莫里斯·谢瓦利耶所观察到的,“考虑另一种选择”),这种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manbet手机版大学校园也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远离生活。manbet手机版罗伯特·戈欣曾说过:“如果你觉得自己双脚都踩在了平地上,那么这所大学就辜负了你。”manbet手机版正确的。manbet手机版但是谁愿意把它种在地上呢?manbet手机版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manbet手机版这本自传/传记是在获奖时写的,后来以丛书的形式出版manbet手机版Les大奖赛诺贝尔/manbet手机版诺贝尔演讲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狗万世界杯诺贝尔奖manbet手机版.manbet手机版这些信息有时会随获奖者提交的附录而更新。
manbet手机版即将到来的
manbet手机版2022年诺贝尔奖公布
manbet手机版查看完整时间表